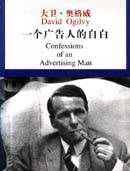两个人的车站-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染说:“爸你这是干什麽,我根本用不著这麽多衣服,带也不好带,带去了哪有地方给我放?还有这些毛衣棉袄有什麽用?”
当时的家庭连生七八个孩子都不奇怪,白染是独生子,从小被母亲溺爱的滋味也并不是那麽舒服,总有那麽些尴尬的感觉,看到父亲为自己忙里忙外,也不太情愿。
父亲说:“你是没吃过苦,出门在外,想置办个什麽都不方便,现在是天热,可是马上冬天就会来的,天寒地冻的,一冷就是好几个月,你怎麽过?到时候哭爹喊娘的又有谁理你?”
说到“哭爹喊娘”,父亲突然有些不自在了,白染也有些堵,说:“我这不是担心你没衣服穿吗?”
父亲说:“哪个要你来担心?我在城里要什麽都还能想办法。再说了,你这走了,咱们父子两个以後都不见得有机会再见面了。”
白染听到这不吉利的话,“唉”的一声叹了口气,转身去收拾书去了。
两个人的车站14
家里的书很多,白染这也想带那也想带,父亲说:“只要想看的,全都带上吧。”於是两个人花了大把时间捆书。
真正出发是在九月初,暑热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不用在路上被太阳烤,轻松了不少。集合地点是在工人体育场。所以父子两个要先把行李运到体育场,才能装车带走。父亲从居委会借了一个小板儿车,还是不能一次运完。第一趟只拉了衣服箱子,卸在体育场上,白染坐在旁边守著,父亲再回去拉第二趟。
当时很讲究集体行动,那一天是市里通一安排送毕业生,体育场上热闹非凡。有竖起的牌子标志下乡的地点,不过还是一片混乱,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也许过了今天,要好的同学朋友就再没机会见面了。白染并没有看到认识的同学,这很好。唯一值得告别的,是邹琴,但她并不在她的那一组标志牌旁边,应该也是找同学说话去了。白染不再找谁,老老实实地坐在“黄平乡”的牌子底下。跟他一组的人陆陆续续地到了,白染才发现,这一组八个人,除了自己以外,有七个女孩子,这男女比例搭配得,太不正常。白染暗暗咋舌,但也不怎麽关心,他对女孩子兴趣不大,可同时也觉得,男孩子还要更难相处一些。
几个女孩子唧唧喳喳的,聚成堆很大声地窃窃私语,理所当然地把白染排除在圈子之外。白染不在乎这麽,而是在比较大家的行李,最後得出结论,自己的行李真是带少了。几个女孩子的行李还要再比他多得多了,甚到还有人带了开水瓶、钢精锅,看那架势,恨不得连自家的灶台子都一起搬去。
父亲路上走了很久,回来的时候,送行的车队已经来了。自己的这一组明明并不是人最少的,可别组派的都是东风大卡车,自己这一组却是派的前进牌小货车。同组还有七个女生,行李都可以堆成山了。几个女生的家长跟白染的父亲嘴上寒暄,手上却不客气,赶著直搬行李。白染父子两个都身单力弱,众人白眼看著他们,都没有帮手,两个人花了好大工夫,还要跟别人讲尽好话,腾点位置出来。就听到有人说:“一个男孩子哪来这麽多东西。”也不能说人家讲错了,实在是这辆车太小了。驾驶室坐了两个司机,不能再坐别人,车斗又窄又浅,堆行李都很勉强了,更别说坐人了。几个女孩子先爬上车,在靠前的位置坐著,手抓著驾驶室後的栏杆。白染只能坐在车尾,颤颤巍巍的。
广播里开始放语录,震耳欲聋,这是在催促大家出发了,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都嘻嘻哈哈的。白染却觉得异常沈重。别人的父母都在唠唠叨叨地叮嘱自己的孩子注意这个留心那个,自己的父亲却一句话都没有说,面无表情,身形落寞。白染说:“爸你回去吧,我这麽大人了,不会有事的。”
父亲没有动,也没有回答他,眼睛不知道在看著哪里。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动了,白染想说一句再见,却还是没有说出口。父亲站在原地,微垂著头,弯著腰曲著脖子,那身影越来越远了。
两个人的车站15
白染的鼻子很热很堵,一个女孩子瞟了他一眼,他不愿意当著她们的面哭,拼命忍住了。另外的七个女孩子原本是同校同班的,这时候唧唧喳喳说话说得很起劲。其中一个向白染搭起话来,问他是哪个学校的,白染也就跟她有问有答,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李红英。
一般都是这样,近郊的条件会比偏远的县乡要好一些,没有人能为白染张罗,他就只能去到最偏远的黄平乡,另外七个女孩子家境都很一般,被分派去黄平乡算是运气非常不好了。车向东开出,过不了一会儿就看见周遭越来越荒凉,路面也越来越窄,一直开进了一片山路当中。白染这才明白,为什麽自己坐的这辆车会这麽小,因为大车要通过这样的泥泞窄路太困难,而且路的一侧还是悬崖,小货车走得都很勉强。
路确实很远,再加上路面坑坑洼洼,车开得很慢,所以大清早出发,得一整天时间才能到达,如果不顺利的话说不定得拖到晚上。几个人带了点东西当中饭,还带了水壶,就像春游一样。要上厕所也很简单,叫一声停车,就钻路边树丛各自解决了,其余时间,只能聊天,车那麽摇晃,要看书看报也不可能的。女孩子的闲聊,大多是议论别人,比如某某的父亲如何如何有地位,不费工夫就能进工农兵大学,又或者某某如何善於跟书记拉关系,分配时去了一个多麽先进的大队,还有某某,求爷爷告奶奶地才勉强跟自己的男朋友分配到了一块儿,可惜那个男孩子又对她不是太上心。这种话题实在让人心生不快,现实的确就是这麽惨淡,可是反反复复地讲,只会让心情更加烦躁。白染搞不懂为什麽女孩子这麽喜欢说长道短,当然她们也完全没有让他一同加入的意思,顶多偶尔瞟他一眼,再低著头窃窃私语。明明昨天睡得很早,可在这嘀嘀咕咕的声音当中,他也越来越困了,把行李勉强挪出一小块地方,靠著一个箱子睡著了。
突然急刹车的时候,白染醒了一看,已经到了地方了,太阳还没有下山。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了车。李红英说:“白染,帮我们把行李搬下来。”
白染楞了一下,想著这意思是不是要自己一个卸下所有的行李。还好就在这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小夥子跳上车开始搬行李了。
车是停在村口,路边站著一排人是来迎接他们的。有村长村支书,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村民。村长是个红脸大汉,额头上深深的几条杠杠,看上去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村支书是圆脸,看上去就滋润很多,也比较年轻。村长很热情,走过来说:“欢迎欢迎。”也许不太擅言辞,只有这一句话而已。村支书也跟著过来说:“欢迎欢迎。”
白染顾不上行李了,跳下车来。李红英很会说话,叽里呱啦地说:“多谢您拉,还特地出来接我们,以後要给你们添很多麻烦拉。我们还什麽都不会,要靠大家多多指导。”白染什麽都不会说,只能跟在後面陪笑,四周都是陌生人,他想,自己的笑容一定很僵硬。
两个人的车站16
村长说:“你们指导员没有一起来吗?”
圆滑的李红英一听这话也有些楞住。她们的指导员就是她们班的数学老师,一个姓王的女老师。暑假返校的时候,王老师跟她们开了个小会,告诉了她们分配的地方,简单聊了聊天。之後她们就再也没见过面。早上集合的时候,体育场上人太多,李红英就算再精,也想不到指导员也要来。
村长到底老练些,看到她的表情就知道是怎麽回事,打著哈哈说:“是我不懂。我以为你们几个学生出们,要麽就是有老师送,要麽就是有家长带。自己来了也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乡亲人都很好,不会怠慢你们的。”
李红英也就信了,没再问下去。
村长说:“村里公社办公室後面是个大场院,还有一间大屋子空著,我已经安排人打扫过了,你们就住那儿。狗子妈会给你们做饭,我招呼过她了,早中晚三餐都少不了你们的。”
几个人有些疑惑“狗子妈”是谁,後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村长的老婆。这一个村都姓赵,外姓的只有各家媳妇。取名字要排辈份,同辈的名字里都有同一个字,所以时常用昵称。村长大名是赵平坚,所以昵称为老坚。村长有三个儿子,小名都叫狗子,依次为大狗二狗三狗。村长就昵称自己老婆为狗子妈。
村里几个小夥子已经把行李卸了下来,村长摆著手,说:“动作麻利点,小心搬过去,别把东西给摔了。”
人家是要帮忙女孩子拿东西,白染就得自己搬自己的了。大箱小箱的,实在麻烦,巴不得当初没带这麽多就好了。正在这时候,一只手抢先提起了两个大箱子,一个声音说:“很重吧?我来帮你提。”
这个声音突然冒出来,把白染吓了一跳,不过声音本身非常动听,不是像他父亲那样沙哑,也不是像当时的电台播音员一样高亢刺耳,而是低沈柔软的。
白染回头的时候,七个女孩子也在看他。这是个外表有些邋遢的青年,穿著时下学生爱穿的长袖,一条军绿裤子,裤脚裁成奇怪的形状,白衬衫上染著陈年的不知所谓的污渍,一双球鞋又脏又破,一头乱发在前额纠结得一塌糊涂。但是在一片乡野山间,这个人就是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他身材算不是魁梧,可是比起大数男孩子,都明显要高挑一些,一张脸并不方正,可是看起来就是很引人注目。当时的女孩子著迷的,是电影里面李侠或者少剑波那样的角色,可是这个人看到女孩子眼里,有另一种奇特的魅力。这个人在笑著,可那种笑就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眉毛轻轻挑著,眼睛微微弯起,嘴角拉出一道懒洋洋的弧度。白染觉得心里怪怪的,但又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於是也就不知道该说什麽。
村长咳嗽了几声,说:“小余呀,你能来帮忙,很好很好。”
两个人的车站17
小余嘿嘿一笑,说:“村长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村长又咳嗽了一声,不说话了。
小余眼光很厉害,一提就提了白染最重的那几箱书。白染不好意思了,说:“那几箱很重的,我自己来提了。”
小余咧嘴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说:“你还没干过农活吧?手劲肯定还是不行。就不要逞能了,小心把你那细津津的脊梁骨闪断罗。”
白染脸一下子就热了,被人看扁的滋味很不好受,但又不能不感激人家,只能说声谢谢,提起了装著衣服的几个箱子。
几个女孩子的行李已经有人在搬了,突然看到杀出这麽个人来帮白染搬东西,都有些酸溜溜的。李红英转开脸撇了撇嘴,觉得如果不是白染从中作梗的话,自己应该能跟他说说话才对。这麽一个大好青年,献殷勤竟然献到白染那麽个书呆子身上去了,真是浪费。
女孩子们也提上了一些脸盆饭盒之类的杂物,进村去了。
黄平乡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原本环境不错北面靠山,南面有溪沟,村里人不多,但是过得相当安稳,只不过跟其他村镇隔得太远,方位又偏僻,路又不好走,所以越来越显寒酸。原先山上种了许多果树可以贴补贴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全给砍了,好在祠堂没被拆掉,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蓄水塘养鱼也是行不通的,莲藕菱角之类也不行,都会被批成走资派,村里人只好辛辛苦苦多开梯田,多种点稻子包米棉花,这样一来,往山上引水就成了大问题。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种革命稻的时候,黄平乡也种不起来,实在是地形本来就不适於种稻。
踩著高低不平的细土路,一路上坡,一条路走到头就是村公社。几个人本以为安排住了公社办公的院子不会受亏待,到了一看,心凉了个透。这哪里是办公室,活脱一鬼屋。难为村里到现在还一直保留著这麽破的老屋,土墙斑斑驳驳,屋顶看上去也让人很不放心,瓦片参差不齐,不知道多久没整休过了,甚至还竖著几撮杂草。窗户上装的不是玻璃,而是新糊上的薄牛皮纸。这样的房子,不能挡风不能避雨,根本不敢想象竟然要在这里长住下去。
进了屋子,地方倒是很大,别说住人,连开大会都可以了。墙上的黑板都还没有拆掉,四面全都是人民公社的标语。四面都是窗子,本来应该很敞亮,可惜光线都被牛皮纸遮住了。屋里开会时的凳子全都被搬走了,泥巴地面上留下了许多凳子脚戳出来的坑,取而代之的是靠墙的一排木头床铺。布置得倒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