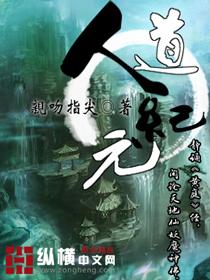妻子与情人-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玩儿”这个词,夏兄是陌生的,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新中国最为困难的时期。在他略略懂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家庭里少了一个人,那便是自己的父亲。他拉着母亲的衣角,哭哭啼啼地追问着父亲到哪里去了,怎么几年不见回家。母亲流干了涟涟的泪水,哽咽着告诉儿子:就在你出生后不到一个月,你父亲就死了。他是饿死的。
为了保证新生儿母亲的Ru房不致干瘪得流不出一滴奶水,夏兄的父亲把从山上找来的地衣、树皮、猪根子等野粮全都给了产妇,自已以凉水充饥。这样过了十来天,父亲的眼睛昏花了,腿像被污水浸泡过的葵花杆,一阵风来也可以折断似的。他终于昏阙过去。产妇嘶声嚎哭着,折腾老半天,丈夫才醒了过来,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本来就没饭吃,你还这么哭天哭地,浪费了体力多可惜!”
说完这句,他的双眼无力地闭上了,干裂的嘴唇蠕动着:“我……想……吃点儿……干饭……”产妇是明明白白地听清楚了,她开始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地寻找丈夫挖回的野粮。然而,早已空空如也。
产妇心一横,将婴儿用条破裤子一裹,扛了锄头就到山上去挖。
满山都是挖野粮的人群,他们提着月亮锄,背着背篓,一双双眼睛,四下里逡巡着。树被去了衣,地被剥了皮,这一方水土已为饥饿的人们作出最大的贡献了。它也无能为力了。
粮没挖到,却收获一背篓凄楚的歌:
太阳落土四山黄,
我在山上挖野粮。
树剥皮来地去衣,
背篓空空往回去。
咿呀呀——
祖先爷也,我饿哟!
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刻,产妇听说乡上某干部要连夜赶往六十里外的县城去办一件事。县城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想必有烧饼之类的东西出售。产妇立即找到那干部,跪着求他一定买一个饼回来。
那干部拉起妇人,泪流满面地说:“我这里还有几两粮票,一定给你买一个回来。”
妇人在干部的家门前等了差不多一个通宵。
清晨五点,干部回来了,两手空空。
“我跑遍了大半个县城,没有卖饼的,只有一个小店卖稀饭,我进去蘸着盐巴吃了一碗,本想带一碗回来,哪知我吃的是最后一碗了!”干部痛心疾首。
妇人绝望了,长嚎道;“我的先人达达也,你到县城嘛,风也抓一把回来嘛!我的人呢,啷个得了哦!嗯——”干部屋也不进,赶到妇人的家,探了探躺在床上的瘦骨磷峋的男人的鼻息,对妇人说:“继续给他喂水,他一时不会过去,我立即再到县城去,把全城转完,买不到东西誓不回来!”
说完,他摇摇晃晃地走了。
天快黑的时候,干部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吃力地旋开来,送到奄奄一息的男人嘴边。
那是他从医药公司买的止咳糖浆。
男人喝完那瓶甜甜的止咳糖浆,满意地死去了。
那风尘仆仆的干部,眼眶湿润了,他没有对死者的家属说任何话,默默地离开了妇人的家。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他饿死在回,家的路上……饥饿,给夏兄的人生上了深刻到骨髓的第一课。他从小就开始劳动,和母亲一起,满山扯梭草,剥烨树皮艰难度日,并供自己读书。在他高中毕业刚刚走上小学讲台的时候,母亲病死了,留下他孤身一人。他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深深地埋藏在书堆里了,并在其中消蚀着天赋和灵性,变成书虫。
他何曾尝过“玩儿”的滋味儿呢?
更何况是与一个女同学一起!
“我还有四十页读书任务呢!”夏兄说。
“你这一辈子,除了书,难道就不需要点别的吗?”
这倒把夏兄问住了。说真的,他对这个问题连想也没想过。
“把你那破玩意儿收起来吧!”明月几乎是带着命令的口吻说。
()
夏兄悻悻地合上了书,跟明月走出来了。很明显,明月竟然把他朝拜的书称为“破玩意儿”,夏兄是很不高兴的。
他们从后校门出去,缓缓走进数百米外的大操常这是一个公共娱乐场,名叫西门操坝。此时,操场上热闹非凡,打羽毛球的,举行篮球比赛的,舞剑的,练气功的,无不透出虎虎生气。明月和木偶人似的夏兄在操场内这儿走走,那里转转,无聊得像两只吃饱喝足的蜻蜓。夏兄似乎害怕热闹,害怕声音,对这一切厌烦极了,痛苦地沉默着。他完全是被明月牵着鼻子走。明月见他那副神情,恶作剧的心态支使着她,专把夏兄向热闹处带去。
他们到了操场的东北角。
这里围聚着数百人,梯子上站着一个瘦瘦的老者,正有声有色地说着评书。
明月知道,这是通州文化馆开办的“广场文艺”,每周末的晚上举行一次。
今天说的是“李白戏贵妃”。
评书的内容,大半是虚构的,说书人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在一星半点的历史痕迹上浓重涂抹,引得众人的喝彩。
明月带着夏兄挤进人群中,她成心要让这一个书呆子受一受折磨。
可是,她完全想错了。
不过一两分钟时间,夏兄就听得入神。说书人每讲出一句,他都要和众人一起,张开嘴大笑不已!
明月气得咬牙切齿,拉起夏兄就离开了。
脱离了那公众的环境,夏兄立即又恢复了他原有的神态,见一个女孩子拉着自己的衣袖,像被火烫着一样,倏地挣脱了。
从此,夏兄培养起了听评书的兴趣。
但评书不是天天都有的,平常,除了上课和买饭,他依然把自己关在那臭烘烘的屋子里。
明月却不给他这种安宁,她频繁地去找他,听讲时也有意和夏兄挨在一起,弄得夏兄毛毛躁躁的。吃过晚饭,明月总是碗也不洗,重重地往桌上一扔,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门找夏兄去了。
夏兄反感到了极点,他勉强忍受几天之后,终于耐不住性子,恶狠狠地对明月吼道:“你去找姚江河好不好?!”
“我不找姚江河,偏要找你!”
明月的声音比夏兄还要响亮。可是,说完这句,她都禁不住泪水长淌。
夏兄是读不懂她的泪水的,他几乎是惊慌失措地跟着明月出了门。
明月像牵着影子似的,把夏兄带到各种娱乐场所。在这当中,明月自己对生活的兴趣一点一点地死去,相反,夏兄那业已于涸的善良的情感却奇迹般流淌出汩汩的清泉。
直到这时,明月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无聊,多么卑鄙。她完全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欺骗了夏兄纯净的感情,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虽然,在她变态的行为之中唤醒了一个人的灵魂,但她的最初的动机,彻头彻尾是一种欺骗!明月痛苦了。她痛苦的原因,一是她时时刻刻注视着的,依然是姚江河的身影,哪怕与夏兄并肩而坐,她的头脑里也会幻化出姚江河的形象气味。一是她本身的善良,不愿意把夏兄欺骗太久,伤害得太深。然而,快到不惑之年却未有点滴社会经验的夏兄,更没有与女性接触的经历,他无法判断自己面临着的危机,更无法辨别自己的可怜处境。他对一切都是认真的。正是这样,明月虽然几次想在夏兄面前坦白承认自己的卑鄙,真诚地向他认错,乞求他的原谅,可话到嘴边,她又咽回了肚里。明月无法想象夏兄听到这些话时会出现什么可怕的景象。她尽量地依着夏兄。周末的晚上,夏兄想到西门操坝听评书,明月尽量陪他去;夏兄要明月帮助他查找有关屈原《离骚》的资料,她尽量爽快地答应。然而,越是如此,明月越是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失落。
前几天晚上的一次奇遇之后,明月再也忍受不住了。
夏兄吃了晚饭,急匆匆地就来找明月(现在,不是明月去找他,而是他来找明月了)。明月正在寝室里翻阅《读者》,正被细小的事物中蕴藏的崇高精神感动着,听到粗鲁的敲门,知道是夏兄。她几乎是怀着厌烦的情绪将门打开。夏兄一脸的汗珠,嘴里还在啧啧有声地吸溜着,大概是他晚饭吃了过重的辣椒,因为他的嘴唇上还沾着一块辣椒皮。
“我终于考证出了杨雄与班固论《离骚》的共同点。”
明月没有作声,坐回凳上,自顾自地翻阅《读者》。她对夏兄这一套已习惯了,分明是早已大白于天下的结论,他却兴致颇高地称是自己考证出来的。
夏兄十分激动,他站到明月身边,口齿不清又喋喋不休地说:“第一,对《离骚》的评价,杨雄与刘安、司马迁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班固的对立面。前三位都认为《离骚》如好色而不淫的国风,如怨绊而不乱的小雅,蝉蜕污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以此推去,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团却认为《离骚》未得其正。第二,在评价屈原的人品问题上,班固与杨雄也有根本分歧,班固认为屈原非明智之器,只算得一个妙才,杨雄却称赞屈原具有盥烨烨之芳草的思想品质。第三,在道德原则上,他们评价屈原也不相同……”明月实在听不下去,没好气地说:“够了!这些问题,查看黄教授的《屈原史稿》好了,你劳神费心去考证,太难为你了。”
夏兄立即噤了声,颧骨上的肉不停地跳动,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明月继续看书。
夏兄侍立一旁。
过了许久,明月的心软了,语气柔和地说:“站着干什么?坐吧。”
()好看的txt电子书
夏兄感激地顺从了明月。
“你吃饭了吗?”夏兄问道。
明月摇了摇头。
“我本来想给你买上来的,又怕你怪我多事。”夏兄委屈地说。
明月凄苦地笑了笑。
“我去给你买吧。”夏兄说着起了身。
“不用了。我一点也不饿。”
夏兄坚持要去。
明月的无名火又上来了,厉声说:“我说过不用了嘛!”
夏兄退了回来。
见夏兄那一副小心谨慎的模样,明月立即就后悔了,在心里狠狠地痛骂着自己。
“你这么不耐烦,心里装着不愉快的事吗?……今晚,我本来想写论文的,现在不了,我陪你出去散散步,行吗?”夏兄蹲到明月的面前说。
明月的眼眶湿润了。“怎么不行呢?你不来找我,我就要来找你的”夏兄感动得搓着双手。
他们迤逦往镜花滩而去。走到中途,明月正与身后的夏兄说话,见没应声,她转身一看,夏兄不知踪影。
明月奇怪地站于原地等了几分钟,才见夏兄圆圆的头一冒一冒地从后边跟来。
“哪去了?”
“嘿嘿,没到哪去。”夏兄憨憨地笑着。
明月也不追究,和夏兄一前一后,沿水泵厂外的土路一直走到滩面上。
其时,天已黑尽了。
这正是五月的月末,淡淡的月亮早早地升上来,混合着对面迷蒙的华灯,把整个滩面照得一片银白。不知是视觉的误差,还是实有其事,滩面竟然在夜色中蒸腾起烟一样的淡紫色的雾岚。明月沉醉了,她伸出手来,想把雾岚拥抱于怀,可近前看去,除了膝陇的白光,什么也没有。但是,在伟大而神秘的自然界中,明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博大的关怀,心情也开朗明净得多了。
那一夜,明月的话出奇的多,比她与夏兄相处一月来说话的总和还要多。
一种巨大的幸福弥漫着夏兄的全身,这种幸福是奇特的,似来自母亲般的温暖,同时,比母亲的温暖又多了一层新鲜的,从未体验过的惊喜。因此,他拙劣的言辞变得畅达了,迟钝的心智变得活泼了,一种让他自己也颇感吃惊的男人的力量,完善着他的人格,滋长着他的自信。他竟然变得洒脱起来。
“我给你带了件东西来,不过你要闭上眼睛。”夏兄说。他说这话时,再不是先前那一副巴结的、乞求似的模样,而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口气,充分地占据着主动权。
明月为夏兄的这种近乎命令似的口气而感到暗自欣喜。在大多数女人看来,男人带着命令的口气说话或者发怒,就像男人看见女人啼哭一样,有种特殊的魅力。
明月笑了笑,将眼睛闭上了。
随即,明月感到一阵扑鼻的香味。夏兄将一支蛋卷放进了她的嘴里。
一股六月里饮了清泉似的感觉流进明月的肺腑。是的,她着实有些饿了,经这支蛋卷的诱惑,沉睡的胃袋被惊醒了,发出低沉却兴奋的吼声。明月闭着眼睛,一直将那支蛋卷吃完,才将在朦胧夜色中发出幽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