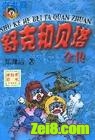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2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突然有声音打破了沉寂,回头一看,是李莲英正推开了门,门外是慈禧太后。皇帝急忙起身,亲自上前搀扶。
慈禧太后就在皇帝原来的座位上坐下,看一看桌上的抄件问道:“都看完了?”
“还没有。只看了吴可读的一个折子。”
“唉!”慈禧太后微喟着:“都是姓吴!”
言外之意是,同为姓吴,何以贤愚不肖,相去如此之远?这也就很明显地表示了慈禧太后的态度,对于吴大澂一奏,深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也就是对醇王存着极重的猜忌之心。
这固然是皇帝早就看了出来的事,然而慈禧太后却从来没有一句话,直接表示对醇王有所防范。皇帝觉得这种暧昧混沌的疑云,如果不消,将来的处境,便极为难。不仅自己会动辄得咎,甚至深宫藩邸之间,隔阂日深,更非家国之福。
因此,皇帝脱口说道:“儿子奇怪,当时醇亲王何以没有奏折?”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深看了他一眼,不断地慢慢点头,呈颇为嘉许的神态,“你这话问在关键上。事理上头是长进了!”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李莲英说:“去!把我梳妆台右首第一个抽斗里面的那只小铁箱拿来。”
“是!”
等李莲英一走,慈禧太后向皇帝又说:“醇亲王当时卷在漩涡里头,不便说什么。好在他早就说过了,等李莲英一回来,你就知道了。”
李莲英来得很快,携来一具极其精致的小铁箱,镀金凿花,是英国女皇致赠的一只首饰箱,有锁而无钥匙,跟保险箱一样,用的是转字锁。慈禧太后一面思索,一面亲手拨弄,左转右转转了好半天,到底将箱子打开了。
“你看吧!”慈禧太后说,“没有吴大澂奏折,今天我还不会给你看。最好你永远不必看,太平无事。”
皇帝悚然、肃然地接过来,翻开一看,是醇王的奏折,于是先看折尾,日期是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是十四年前的话。
“你念一念,我也再听听。”
“是!”皇帝不徐不疾地念:“臣尝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
读到这里,皇帝不由得就停了下来,因为这是醇王开宗明义,有所主张。而提到旁支入承大统,不是谈宋英宗的“濮议”,就是论明世宗的“大礼议”,不知道还有宋孝宗的故事。
皇帝只记得由宋孝宗开始,宋朝的帝系复归长房,也就是由太宗转入太祖一系。孝宗为太祖幼子秦王德芳之后,生父名叫子偁,如何得封秀王,可就记不起来了。
“你怎么不念了?”慈禧太后问。
“儿子在想,秀王子偁是怎么回事?”皇帝答道,“儿子念《宋史》,倒不曾注意。”
“我告诉你吧。”慈禧太后身子往后靠一靠,坐得更舒服,双手捧着一杯茶,意态悠闲地说:“大宋天下是赵匡胤的天下,赵光义烛影摇红,夺了他哥哥的基业,所以金兵到开封,二帝蒙尘,子孙零落。这是报应!”
皇帝读过《宋史纪事本末》,对于这段所谓“金匮之盟”的史实,记得很清楚。当时杜太后本乎国赖长君的道理,遗命定下大位继承的顺序,兄弟叔侄,依次嬗进。赵光义兄终弟及之后,应该传位魏王廷美,再传位燕王德昭,天下复归于太祖的子孙。结果是赵光义背盟,六传至徽宗而有金兵入寇,国破家亡之祸。时隔一百五十年,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如今为慈禧太后轻轻一句“这是报应”而绾合在一起,皇帝不由得心头一震,泛起了天道好还,报施不爽的警惕。
“宋室南渡,高宗只有一个儿子,三岁的时候,得了惊风,小命没有能保住,高宗从此绝嗣。那时候,吴后从江西到杭州行在,得了一个怪梦,”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是个什么怪梦?没有人知道。想来总不外乎因果报应,梦中示警,倘或高宗不能悔悟,为他祖宗补过,一定还有大祸。这个怪梦,吴后说了给高宗,高宗就决计拿天下还给太祖的子孙。降旨访求太祖的子孙,第一要‘伯’字辈,就是高宗的侄子;第二要七岁以下;第三要贤德。结果初选选了十个,复选选了两个,一个胖、一个瘦。胖的是福相,自然占便宜。”
“那就是孝宗?”
“不是!”慈禧太后喝口茶,极从容地往下讲:“瘦的赏了三百两银子,已经要打发走了,高宗忽然又说‘再仔细看看!’就再看。两个人并排站在那儿,有只猫从他们脚下过,瘦的不理,胖小子淘气,一脚就踹了去,这一脚把他的皇帝给踹掉了。”
“怎么呢?”皇帝兴味盎然地问。
“这就叫‘观人于微’。”慈禧太后略略加重了语气,使得这句话带着一种训诲的意味。接着又说:“离宗当时便跟左右说:”这只猫偶尔走过,又不曾碍着他什么,干吗踢它?本性这么轻浮,将来那能治理天下?‘就把瘦的给留了下来,这才是宋孝宗。现在要讲孝宗的父亲,就是封秀王的子偁“
子偁是高宗的族兄。徽宗宣和元年,宗室“舍试”合格,调补“嘉兴丕”,这年生子,取名伯琮,就是后来的孝宗。伯琮被选入宫教养,子偁父以子贵,但也不过升到五品官,十几年之后病故。其时伯琮已受封为普安郡王,子偁恩赠为太子少师。普安郡王被立为太子,子偁才追封为王,因为嘉兴又称秀州,所以封为秀王。
“后来高宗内禅,孝宗做了皇帝。秀王是他生父,不也该追尊为皇帝吗?”慈禧太后深深看了皇帝一眼,似乎咄咄逼人地等着答复。
皇帝最畏惮她这样的眼色,自然而然地将头低了下去,默念着醇王奏折上的那句话:“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恍然大悟,醇王自愿地表示,他决无非分之想。
既然自己父亲有此意向,而且醇亲王的封号,眼前也决无更改的可能,那就聪明些吧!皇帝这样在想。
“无论国事私恩,从那一方面看,都以不改王封为是。”
“噢,”慈禧太后似有意外之感,“你好象很有一番大道理可以说?”
“是!儿子也不敢说是大道理。”皇帝答道,“论私恩,孝宗七岁入宫蒙高宗教养成人,这番抚育深恩,自然永永记在心头,而况又付托大位?裁成之德,过于生父。当时高宗内禅,退归德寿宫,如果孝宗追尊秀王为皇帝,称为‘皇考’,岂不伤老人之心?”
“嗯,这是私恩。国事呢?”
“宋室南渡,偏安之局,凡事以安静为主。如果追尊秀王为皇帝,于礼未协,必有人上书争辩,就象英宗朝的‘濮议’那样,自非国家之福。”
慈禧太后静静听完,脸上浮现出恬恬的神色,“你说的道理很透彻。如今真该以国事为重!”她说:“你再往下念,听听你‘七叔’说的道理。”
于是,皇帝接着念醇王的奏折:“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抵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虽立心正大,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
“也不多。”慈禧太后突然插进来说:“如今只有吴大澂一个。他拿乾隆圣谕作挡箭牌,你能说他不是‘庄论’吗?真亏得你七叔见得到,早有这么一个折子,可以塞他的嘴。你再念!我记得这就该提到你了。”
慈禧太后没有记错,下面正是提到皇帝入承大统之事:“恭维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至隆极盛,旷古罕觏。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之徒,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徒滋多事矣!”
念到这里,皇帝想起张璁六年功夫由一名新进士当到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的故事,不由得憬然自警,特地停下来说道:“儿子不会听那些‘危言’的!”
“原要你心有定见。”慈禧太后不胜感慨地说:“不想草茅新进倒都安分,做了几十年官的,反而这么飞扬浮躁。”
这是指责吴大澂。皇帝停了一下,见慈禧太后别无议论,便又往下念:
“合无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亲亲政时,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
千秋万载勿再更张。“
醇王的建议,不仅止此,还有更激切的话:“如有以宋朝治平、明朝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是不但微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所有微臣披沥愚见,豫杜金壬妄论缘由,谨恭折具奏,伏祈慈鉴。”
原奏是念完了,因为内有“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的话,所以皇帝接下来便请示,除了宣示原折以外,是不是还要将吴大澂革职?
“不必!”慈禧太后的态度很平和,“本来我连这个折子都不想拿出来,如今看来,倒象你七叔不幸而言中了!既然吴大澂有那么一种说法,原折似乎不能不发抄。读书人看重的是声名,你七叔的折子一发抄,吴大澂也许自己就会告老了。”
※ ※※
一夜过去,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最后一天,也是皇后初次朝见太后的一天,这天也是皇帝亲祭社稷的日子。内务府官员分几处照料,忙得不可开交,当然最要紧的是照料慈宁宫的典礼。
皇后朝见太后的吉时,钦天监选定辰正,也正就是平时慈禧太后召见军机的时刻。为了不误吉时,只好提早跟军机见面,又为节省工夫,破例改在慈宁宫召见。
这天必须请懿旨的,就只是与醇王有关的两个奏折。一个是吏部复奏处分屠仁守一案,孙毓汶秉承醇王的意思,决定严办。同时打击吏部尚书徐桐,为了报复他反对修建津通铁路。
这个折子已经交议,所以先由礼王世铎出面复奏,“吏部办事,实在有欺蒙的嫌疑。奉旨交办事件,那可这样子敷衍?明明是有意包庇屠仁守。”他说:“臣等几个公议,屠仁守违旨妄言,过失不轻,吏部议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已嫌太轻。御史开缺之后,又不把应补什么官叙明。如果前一个折子奉准了,屠仁守不过由御史调为部员,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
“屠仁守应该革职,永不叙用。吏部堂官交都察院议处,承办司员,查取职名,交都察院严议。”
“这样的处分,不太重了些吗?”
“皇太后明见,”世铎将孙毓汶教他的一番话说了出去,“皇太后听政,各部院不敢马虎,如今归政在即,不免松懈。
皇太后如不为皇上立威,以后办事就难了。“
这几句话说得笼统含混,但意思已很清楚。慈禧太后不愿在最后一天跟军机大臣的意见不合,便点点头说:“好吧!
就照你们的意思,写旨来看。“
处分了这一案,就要谈吴大澂的密折了。慈禧太后不即说破缘由,却先打听吴大澂的一切,第一是问他的官声如何?
礼王世铎心里奇怪,何以忽然问起吴大澂的官声,莫非有人参劾?河督虽是个肥缺,但郑州黄河决口,宽至五百五十余丈,朝命特派李鸿章主持修复,前后两年有余,耗费部款数百万,纵有经手人中饱,与吴大澂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是去年八月间才署理河督,秋汛以后,郑工合龙,去年年底实授河东河道总,赏加头品顶戴,不似会出什么差错。倘有差错,首当其冲的也是李鸿章与吴大澂的前任李鹤年。
这样飞快地转完念头,便决定看醇王的面子,说几句好话,“吴大澂是肯做事的人,不怕难,不怕苦。”世铎说道,“操守也还靠得住,除了喜欢金石碑版之外,倒不曾听说他有喜欢别样。”
“他跟醇亲王是不是常有往来?”
吴大澂的奥援就是醇王,与李鸿章处得也很不坏,他之有今日,就是这两个人的力量。此为尽人皆知之事,但世铎却不肯实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一提到醇王与朝官名士结交的情形,便得谨慎,为了怕替醇王招来一个树党结援的名声。
“奴才不甚清楚。”世铎这样答道:“纵有书信往还,想来谈的也是公事。”
“那还罢了。如果吴大澂是受了醇亲王的好处,想有所报答,又不知道怎么样报答,随便上折子,那就不但他本人荒唐,也是害了醇亲王。”慈禧太后拿起吴大澂和醇王的两个折子,“你们看罢!”
世铎接过来匆匆看完,为吴大澂捏了一大把汗,心里在想:这自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