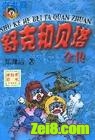����ȫ��-��12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ϰ��£��Ծ��米֮��ļ��⣬��Щ�������䡣
������Ĭ�����������ע����֪�������ߵ������ĵ̫��������������������ů���������ѿ�����������ֻ�ǵ�Ļ�����̵���ڣ������߹���˫ϥһ������ƣ����������Ĺ���ʥ������Ȼ����ڿ�ͷ���չ��ñ���ȷ��ڵ��ϣ�����˫�ۻ���ģ��ð���β���ϣ���һ�������ĵ��ǵã����Ĺ�ͷ���������ǰʱ��ȴ�����ٰ�ñ�Ӵ��ϡ�
����ʱֻ����ǰ��������һ�����ӡ�������������Ҳ����ʾ�������������ԣ������Ĺ����Դ����ڵ����ϡ�
�������ģ�����һ�����ڵ��Ǵ���̫���⼸���������ˡ���
�������ȵ�֪��֮����Ӧ�ý��Ҿ�������
��������һ�춯�������ģ���
�������³����������������嵽���ʮ��������
��һ·�Ͽɰ���������
�������Ժ�����������ǰ����������������ȫ������ʵ�İ��£��������Σ����ղ��Կ�Ͳ������ˡ���
����͢Ҳ����ô�롣������̫�������˵����������������������ֱ���ܶ�������Ҫ���Թ��òźá���
���ǣ��������Ĵ��������������֪��֮������������ġ���
��ʱ�Ȱ�̫�����ˣ����������������ѧû�У���
�������ʽ������ϲ���ʹ�س��佲��ѧ����ʱ�����������٣������������н��Ρ���
��ร����Ȱ�̫�����ʣ���������һ�Ƶģ���
�����ǵ���ʮ�����ɳ�������������ʽ��ʮ��������
��ʱ�Ȱ�̫������������������Ǹ����ˣ����ǽ�ʿ���������ʶ�û���ʶԣ�����Ը��˵���ˡ�
���Ǵ���̫������ʣ���������������ˣ���
�����ڵ�����䣬���ν��������һ���ǵ���ʮ���������������������ʮ���ˡ���
������ʮ���ꣿ������̫���Ź����ʵ��������������������ĺ����𣿡�
���ǣ���������֪�����ĵ�һ�����£����Dz����н�ʿ������֣�ƫƫ����̫��������ʹ�����Գû�����һ�£��������ĵ�ѧ�ʣ������ں��֣����ǽ���ʵѧ���ˡ���
����̫��dz����������̱�ӿ�˵��������͢����Ψ�ţ�ԭ���ڿ�����ͷ�����������ģ��㿴�������ľ���Ҫ����ʱ����ܳɹ�����
���ʵ�Ҫ���ط����ˣ������IJ�������������������������ľ�����˸���ʩ��һ�˰��ˣ��ܵ�����Ĺ����ܰ�ʦ����
����Ĺ����ƺ�̫���ˣ�����һ�˰��ˡ���仰������̫����Ϊϲ�á��������룬�����Ժ����ͬ��ʮ���꣬�ʵ�ʮ���꣬���������ˡ���ʱ��һƬ̫ƽ���£��ָ��ʵۣ����峯�����ˣ�����Ů�����϶Ե����������ڣ��¶Ե����ĺ�������˵ʲô��Ů��Ң˴����Ҫ��Ů�еĺ���ۡ���̫�ڣ��������Ƕ�һ������ǰ�����ʥ��
ת��ˣ�ƮƮȻ���������ˣ������������죡������Ҫ����������������չ���á�����˵�����⼸����պܿ࣬ȫ�����Ǽ���ͬ��Э��������ƽ�ң���Ҳ���̫ƽ���Ӻù�����
���ǣ��������IJ�֪�����������ˡ���ʦ�����ϵĻ����������Ϲ����ᣬ�������ѡ�����
�ᵽ�⻰���Ȱ�̫��������ˣ��������ʮ�˰ɣ���
����������ʮ���ꡣ��
������ͦ�õġ���
���б�ʥ���������罡����������˵�����Ƕ����⼸���ھ�Ӫ���������ġ���
�������ģ�������̫�����ᵽ�����������������Ҫ�ɶ�������һ·���ȥ����
�⻰����˼���������ף������ɶ�����������ʼ��ȷ����������ʵ�������ĵĽ�������������ˣ������漴���ࣺ����������͡����������������������������ȳ��ݴdz�������Ӫ��ɽ�����ٶɺ����¡���
�������Ӻܺá�������̫����˵����ǰ�칧�����࣬˵�����ľ��ã�ÿ���Ҫ������ʮ��������úúóﻮ����
���������ã�ÿ��ʵ���İ�����������������������ﲦ��
�����Ŷ������ȣ������֮�ǣ�����ר��ע��ǰ������
�����Dz�����������̫������һ�£����Ź����ʵ�������ү���㿴��ô��������
�����в��ã�ԭ˵�����塢��ʮ������������˵��ʵ���İ����������������������һ���������棬�����������������������д������������������������������ϸ�鶨�³̣���ּ��������
���ã�������̫����ͷ��������ô��ɣ���
���ǹ�����������֪������ѱϣ�����Ҳ����ͷ��վ���������˺�����һת�������ɹ����Դ������ڹ��������˳����Ѷ���ñ�����������ĵ�ש�����ˡ�
���º���һ���ź������ֿ죬������ǰ����ñ�������������Ȱ�̫��㺰����С���ӣ���
�����������º����´�Ӧ��
����������ĵ�ñ�ӣ����˸�������ȥ����
�����������º���Ӧ�ţ�������ȥ��
��������̫������������Ϊ������ڣ����������������ġ���ɫ�±�һ��ʮ�����������͵������£�л�˶��������ͺţ�ͷһ��̫����ߣ��ڶ���̫���ֵ��ˣ�����һ��ñ�У�Ҫ��������ˡ���
������˵ĺ춥�Ӹ�˫�ۻ��ᶼ���ˣ�����̫�����˵���������ص����ͻ�����
��ร�����������Ϊ�˲����Ͱ��գ����Ժܸ��˵�˵��������Ϊ�㡣��
��������˻ػ�����������滹��֪������
֪���˱���ô���أ������Ļ���Ѱ˼�����ҵ�Ļ�ѻ������Ͻ��յ������ʣ�����˵�����䣬�����ͷ˵�������ԣ��㿴�Ű졣��
Ļ�ѰѰ��º�������̫�࣬�뵽���ң������飬�������⣬��̫��Ҫ��ǧ�����ӣ�һ�IJ����١�
������ô������������֪������������ʷ���������ġ�ʧ�ǡ����ض��ɶ����飬�����������Ҳ�ض���������������ۡ����ͨ����֪��
��һ�¾ͻᡰ�֡���Ц����Ԫ�������������йأ���Ļ����������������������̫���Ҫ�������ı��ˣ�ֻ֪���ַ���һ���ͣ�����֪�����������������������С�£����Զ��ʣ�����һ��������¸����¼��ѡ������ۣ�����̫���������࣬�����ּ���ں�����˰���£�ÿ��ָ���¸ʾ�һ��������
Ҫ�İ���ֻ��һ������������Ȼʧ��������ʱ�������ã��ȴ������أ����������ʵЧ����ʱ�ж�����Ҫ�����ã���ʵ���㣬ָ����Դ�����³�͢���ʣ���������롰�������ܡ��Ӱ졣����ҪЮ�ķ���������֪��������������ѧ�ô���Щ��һ�仰��˵���������ӡ��������̫�ʵۣ����г�����
�����ǰ��¶�ʮ��������������µ����������������»���һ��������Ȼ������¾͡����ա��������ĵ��йݣ�һסס�˲��һ���¡�
����Ϊ���������ƺ�һҪ̸�����¡����ڶ�Ҫ̸�������������¶��dz��鷳����͢����˼������Ҫ���������IJ��ӽ�פ���ܣ���������ְ���ǡ�ֱ���ᶽ�����������Σ�������˳��������������Ϊֱ���ܶ�����˽�����꣬����ܲ���취��������������������������λ��ү���������Ͷ����Ľ�ƣ��ֻ�������ӵ���ξ��ʣ��������긣��˵������ʹ�����������Ϊ�ѣ��������Լ����С�������������֮�ݡ�
����������������������˵������ͷ����˼�����߶�����֧���������н�����ĵط������Ի���Ӧ��̭����ǿ������Ԥ������
������Ǿ���Ը����������ˣ�һ�����Ǵ���̫�࣬һ���桰������Ҳ���ˡ������Ǹ���������һ����̣������ܿ࣬��Ҫ��������ͷ�������˼�����������Ҫ����������
����ү��������ʮ��֣�ص������������������ƣ����Ҳ���ʵ��¡�ƽ���ƽ������ʮ�����ս���ĵã�ֻ��һ�仰����Ȩ�����һ����ƽ�������ۣ����dz�ּ����ү���Ƹ�����ֱ������ô�ཫ˧����������Ϊ����ֻ����˿������������㲻���ԡ���
�ⷬ���Թ�ά������˵������Ȩ�����һ������Ȼ�ܶ���������������ͷ˵�������Ǻ�ʵ�ڵĻ������伾�ߵ�Ƣ������Ҷ�֪�������������˳�֣�������˧����͢��Ȼ�����ƵĴ��á���
��һ˵�������ˣ�����������Ա����ˣ��������ɲ��´����£������ڹ����Ļ�������������˧�������Լ�ȥ�������ģ��Ǿ͵�����ǰ�У���ʮ�궼�����չ�����������¤���ɡ�
����ү������˵�����ߴ�Ř������Ծ�Ӫ��������Ϊƽ��־��֮���ڣ�����������������˿ɡ��ο��������죬����������ү��ǰ˵��й���Ļ�����ս���ѣ����������������ǡ�ǿ��֮ĩ�������Դ�³�ɡ�����
���ǡ�������������������������˵��������֮�飬ֻ��̸����������ˡ���
���ھ��ﱾ����̸����������ġ��������ȫ�����ۣ�������飺���ƺ�����Ҫͨ�̳ﻮ��̭����ǿ��һ�£����ôӺζ���������һ�¡�������Dzһ�£�������������һ�¡�������ƽ���ٷϴ��٣�����������չ����Ҫ��ʿ��ӣ��������òų��һ������֮�������ںδ���Ҳ�������������������õ��������ˣ��ſ���Ӧ������
��������������Щ�ķ����п���˵����Ϊ��ΪȥΪ��һ���֣�Ǯ����
�����ˣ�����һ��Ǯ�֡��������µ������ڶ��ϲƸ�֮����������������Ϊ���ģ�����Ϊ���š���������λ�ܶ������棬�ú�̸һ̸���������üĿ�ˡ���
���ã��������������˾��������������㵽������һ�ˣ�Լ������ɽ��������̸���³̳�������͢����˼��������Ҳ֪���ˣ�ֻҪ����ܹ����ȶ����п�չ��������ô˵����ô�ã���
������ү�ػ����ұ����Ĵ��㣬Ҳ�dz����Ժ��ȵ�������������ʦ�������굽������¡�������������ʦ��ֻ�²��Ͻ�ֱ����ӡ����
������һ�㣬�������ķ��ˡ�����������ֱ����л�������У���û�����ױ�ʾ����Ը���Σ����и�����Ƭ��˵�����������Σ���δ���ڼ����ƣ��ӹ�ʮ�꣬δ��һչ��Ĺ��հ����鱣��Ѱ����¡�����˵������������������֮�£��������Ժ���������ְ�����¶����ϳڣ��Գ���Ǹ֮�ˣ�ٹ����ʱ�����о��ࡣ����˼�Ǿ����ң����ڸþ�Т�ˣ������ݼ�ʱ��һ�������࣬��ٻؼ�ɨĹ���ʹ˴ǵ�ֱ���������������һ˵���ǡ���Ƭ��������֮�⣬Խ�����ס�����µ�Ҫ������ͨ��
���ǹ������˺ܼ���ı�ʾ����������ƽ�Ķ��ۣ�������ʦ��Ҳ����Ϣ��ʱ����������������˭�ǿ��Ըߵ����ֵģ����ο�����ʦ�ĵ����žߣ����������ٲ��ô��ˣ�����ʦ�ܵĸ��鼫�ã��������ΪȰ�ݣ����Ͻ�ֱ���Ļ�����ò�Ҫ˵������һ˵����������ͽ�˸��顣��
����µ���˼һֱ�ܻ�������š���ʦ����ļ��ֱ��������ͷ��Ըǿ�����ѣ�����Ҫ�跨Ȱ�������������Դ��������Ե�����������ʦ�о���֮�⡣�����������Ŀڷ磬�����˲��ɣ�����������ǰ�����������ˡ�
���ǣ����dz����еش�Ӧ������ү����ģ���һ����������ʦ��Ȱ�����ճ�͢����˼������ֱ������
�����ܼ������飬˵�˺�Щ���еĻ�������������м��£�ȴ�����й���������ƽ���ľ��ѣ�ǰ����ȥ��ǧ�������ӣ������������ȴҪ�������������뷨�������ƽ����ľ���һ��������������Ϊ�ˣ��ص�ȥ���������鱦䣧���ސ��ܣ������ʾ�������������ˣ�ĬȻ��Ӧ���Ǿ�ֻ��������취�ˡ�
��һ�������˸���������������飬�뵽��ׯ��С�ã�̽�ʿ�����Ҫ�������ܰ�����ǧ�������ӵı�����˳�����أ�
������ʵȨ������˾�����У�˾���ֱ���������죬����Ҫ�����ء��Ĺؼ�������������ϣ����������������������죬����������������ֲ�ͬ�������������������̡����������������ֵı��⣺��������ƶ������������������죬ռ���������֣�ȴ���ǵ�֮������
��������˾�ٺ���죬���ڲ��������֣�ʮ�ĸ�������˾����ְ�Ƹ�����ͬ����������·�����ˣ�����������ǡ�����˾���͡�����˾������죬����Ϊ����˾���˸�ʡЭ�ã�����˾���˺���˰�գ��ⶼ�뻴��ƽ���ľ��ѱ����������й�ϵ��
����һ�����ͣ�Խ��Ҫ���������ǻ��������������ı���ʽ�����������ʣ��鱱�������ܣ���������������ȷ����ֻ�б�����֪���������˾�����������������˲��㡣ͬʱ�����������˵����Σ��������벻������Ҫ���������������������ڿ˺��ı���ʽ������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