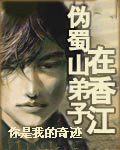香江边上的思考-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疑具有重大的影响,而邓小平也常常被人们看做是实用主义者。这其实是对邓小平的巨大误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因此对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阐述和不断创建被看做是党的生命所在。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在香港问题上,主权归属就是不可以用经济繁荣来交易的政治原则。因此,面对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经济繁荣论,邓小平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定义香港问题。他在谈话的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论“一国两制”》,香港三联书店二○○四年,1页)
首先是主权,其次是治权,最后是过渡。这是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完整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展示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它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香港繁荣问题。在他看来,香港问题的实质不是繁荣问题,而是主权归属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香港的主权是谁的,然后,这个主权者才有资格考虑如何维护香港繁荣。换句话说,在邓小平的理论框架中,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香港主权属于中国,香港繁荣问题属于中国政府要考虑的,与英国人毫无关系,英国人应当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过渡的问题,这才是中英谈判的实质。
正是从主权问题入手,中国政府就掌握了整个谈判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因为它直接回应撒切尔夫人假定的三个条约有效论。新中国成立后曾明确宣布三个不平等条约无效,并重申对香港、澳门拥有主权。一九七二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正式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当年联合国大会将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地化”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删除。这意味着香港的前途不可能独立,而只能回归中国。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主权话语无疑为谈判争取了政治主动权。当年,在中央内部讨论香港问题时,不少经济官员顾虑香港繁荣问题而对是否按期收回香港举棋不定,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发言中慷慨陈词,主张不按期收回香港就等于是李鸿章政府。这种主张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Zei8。Com电子书下载:。 〗
在与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中,他直接提到这个问题,显示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因此,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至于说如何保持香港繁荣问题。当时中央高层的经济官员,都存在类似“主权换治权”的想法,即主权归中国,让英国人继续管治。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机会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他的政治智慧就在于能够在原则与现实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既能满足左派主张的主权回归,也能满足右派主张的保持繁荣。在他看来,香港繁荣不是由于英国人统治,而是由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为此,他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模式来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持香港资本主义的繁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批驳了香港繁荣论,打消英国人以香港作为“下金蛋的鸡”来要挟中国的企图: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页)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未来。香港回归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不能不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远见所折服。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既不是显示实力的粗暴,也不是鲁莽的冲动,更不是出于名留青史的政治虚荣心,而是出于成熟政治家对未来远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刚毅和决心。如果说,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权问题上,也不是在繁荣问题上,而是在最关键的过渡问题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于去除了任何虚幻的东西,无论盲目的迷信,还是天真的幻想。虽然当时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很密切,但邓小平很清楚,在香港问题上,由于涉及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必然会制造各种事端,威胁到香港顺利过渡。为此他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同上,3页)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告诫撒切尔夫人:“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同上,3页)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
这可以说是一种霸道,是在最关键时刻展现主权中最硬的一手,即诉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邓小平展现出支撑政治正当性或正义原则的主权意志,即对紧急状态的决断权。政治意志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准备,更不是鲁莽从事,而是对最坏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准备勇敢地承担。当年,中国人正是准备好“打碎坛坛罐罐”,才勇敢地投入朝鲜战争,最后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而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也做好了香港发生动乱、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坏结果,才宣布收回香港,也争取到谈判的顺利进行和香港的回归顺利。为此,邓小平曾让国务院算笔账,香港每年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外汇,如果香港出现问题,对国家的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主权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法学家博丹为主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帮助欧洲的世俗君主战胜了无所不能的教皇,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这个定义,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主权,而且是人民主权。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无疑是关于主权学说的经典文献。它在主权、治权与政权过渡之间建立了内在的理论关联,王道与霸道杂糅,展现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审慎的判断、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在西方经典的主权学说中,主权就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统治,可是在邓小平所阐述的主权理论中,中国虽然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并没有行使这种主权。这种与西方理论的背离恰恰展现了中国对主权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即区分了“主权权利”与“主权行使”两个概念。在中英谈判初期,通常采用的说法是“主权回归”。对此,著名的国际法学家邵天任先生认为,香港的主权一直在中国,英国人从来没有拥有香港主权,所以不存在“主权回归”问题,而应该是“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赞同这个说法,于是,“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后来就写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也正是这个原因,“联合声明”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因为中英双方没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完全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宣布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既然英国人也同意这个声明,那就自然变成了“联合声明”。
(《戴卓尔夫人回忆录》,香港博益出版集团一九九四年版)
“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七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6期
一支笔,一张报,往往是文人的梦想。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明报》和《信报》当初都是由一支笔支撑起来的。金庸大侠早期给《大公报》副刊写武侠小说,港英政府镇压“六七反英抗议运动”使得左派报纸受到影响,金庸干脆自立门户,创办《明报》,至今受到文化人的推崇,不仅有文化品位,时事评论也充满政治理性。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先生也是靠一支笔创办《信报》,直到今天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专栏和评论。
从宏观经济到财经政策,从内地改革到全球经济走势,从香港政制到大众文化,这些评论充满了独立思考和专业见地,几乎篇篇可读,单凭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就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林行止与金庸的研究领域和写作风格不同,在政治见地上也有区别。金庸在武侠世界中,用边缘文化和少数族裔挑战和质疑中原的文明正统, 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在不同政治和文化夹缝中游刃有余的香港人形象并质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他并没有颠覆正统。于是在整个香港回归年代,《明报》都以乐观的态度主张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林行止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明确主张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三个条约有效论”,鼓励英国政府以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为条件要挟北京,用“主权换治权”,保持香港继续由英国人统治,说到底是对香港回归中国没有信心。对香港的这种普遍民情,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了。而他提出“一国两制”主张使得连林行止这样对香港回归持怀疑和消极态度的人,也都赞成香港回归了。对此,林先生感慨道:
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在政治面前,经济利益算得了什么?特别是受一统思想和民族主义激情所催眠的中国领导人,又怎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在原则上让步?在这一环节,我的看法原本相当准确;可是,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竟会提出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及“港人治港”作为其香港政策指南;不管这些是否权宜之计,都足以令英国及港人无法招架。自从这些石破天惊的特别措施提出后,港人信心问题虽然还是存在,但由于对“高度自治”及“一切维持不变”有所憧憬,“英去中来”对港人所引起的冲击已大为降低。(林行止:《香港前途问题的设想与事实》,香港信报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版)
一句话,中央之所以能够争取到香港人心,使香港在保持繁荣的前提下顺利回归,要归功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中外政治家都一致称赞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构想。然而,想象力何在?想象力从何而来?“一国两制”思想已提出二十多年了,我们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些问题。以至于“一国两制”依然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设计,而没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难以发挥出“软实力”的作用来解决世界各地的类似政治难题(如科索沃问题)。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视野过于狭隘,将其看做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而没有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从毛泽东到清朝开国君主们关于中国边疆政治的连续性思考。而在这思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国两制”无疑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讲这个构想是他自己独创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来华探寻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时,小平重申了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让香港投资者放心。当时还没有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中央同志就明确告诉卡林顿,请他们研究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或者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可见,中央对港政策与当时提出的对台政策以及中央解决西藏的办法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