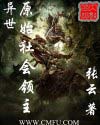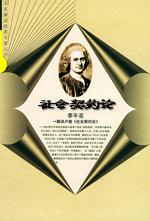���·������-��2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ս�ƽ�����⣬�����Ҫȷ������һ�־������Ӵ�Ĺ��ҹ�Ȩ����ǰ����һ��˽Ȩ������ǽ��
������������ֵȡ��ƽϸ����·���淶���»�涨����Ȩ����ǰ�����Թ�������Ϊ�������룬��ֹ˽Ȩ�������Ӵ������˽Ȩ���Գ�ַ�չ��أ��������ٽ��г����ú�������չ���й����ڶ�Ϊǰ�ߣ������ҷ������»����Ҳ��������ݰ��IJ���֮�����ڴ˳�������ƽ�ᳫ�й��ƶ���ĺ���Ӧ��Ȩ��Ϊ����������Ҫ�ƶ�һ������ʽ�䡣��ֻҪ����û�н�ֹ�Ķ����Դ��£�������Ȩ���Գ����չ�Ŀռ����ء���
�˶��ڡ���ʶ����˵����������κ�״̬�¶���һ�ָ���������������ʹ�����������״̬ʱ��Ҳ������һ�������ѵĻ��������ܶ�Ҳָ��������ν���ɣ���ָ����ͳ���ߵı�Ű�ķ�����������Ȩ�����ü�����Ϊ�����ṩ��һ�ֹ���һ���ı���������˵����Ȩ�־õض�������Ȩ֮�⣬���Ƕ���Ȩ��һ�ַ�����Ҳ��һ�ַ�Ȩ����ʷһ�δ�֤���������Ȩ���ܸ��ڲ���������Ȩ֮�⣬��Ȩ�����Ϊ��Ȩ�ĵ������ܵ��˺���������ʱ�ᱻ�ٻ���Լ���Ƶ�������
ͬ����Ҫ���ǣ������Ȩ�ܹ��õ������ı�����������Ȩ����˵��ʧȥȨ��Ҳ����һ�����˾��������顣����˵����Ȩ��ֻ��һ��Ȩ����ͬ����ζ������һ�ֿ���֧����߲�������Ȩ����������һ�㣬�Ͳ�������Ϊʲô��ʢ���ڶ���ս��������ܾ����������ǻص����Լ�ׯ�����Ѽ��°������ꣻ��ʱ�����գ��й��ĸ������δ��ȴ��ʱʱ���в���������ԭ����������й�����Ȩ������û�н�������״̬��
�������ӻ�����������
�����̤������������Ȩ�ġ����������Ρ������������á����ڳ�Ϊȫ�С�2007������ڡ���Ȩ�����䲼֮ǰ�������йء�ʷ����ţ���ӻ�������Ƭ�����������硣ԭ��ƽ̹�����أ����������ڳ��˽���ʮ����ӣ��м䲴��һ��µ�������ء��µ����棬��һ��ͬ��������Ķ���С¥��С¥��Ȼ���š����ܽ������ܽ������ƾɣ�����ȴ�ԡ������������ܽ���������ѱվ�����
�����ۣ���������������������ƺ���վ�ԡ����ڲ��ܽ��ܿ���������IJ������������������겻��Ǩ������ǰ���˵��;����ˡ�ʷ����ţ���ӻ�����
������һЩ���в�Ǩ�˶�����˷�����ȷҲ�������ࡰ���ӻ��������������ǽ��������ܵ��IJ����������㼯�ɲᣬ���Ҳ��һ�������ġ��������ռǡ������ĸ��ط���Ǩ���������˰�������������ijЩ��Ա�ļ�ֵ�ۻ��ͷ����ֵ�����ҵ��ǣ�����Ȩ���汻���ӵĽ��죬���ڴ��������˵�������ӻ����Ѳ�����һ�������ƻ��Եġ���ʶʱ��ı���ʻ㡣�ӹ�Ȩʱ�����������еġ���˿������˽Ȩʱ���������ġ����ӻ��������Կ�����ʮ����й�������������Ľ�������ѡ�
�����ӻ���ҲҪ����ʽӹ졣��˽Ȩ֮��Ĵ����£����Dz�Լ��ͬ���뵽�˷�����һ����ǰ�IJ���̹ĥ�������£�����һ���йع�����Ȩ�����ԣ���Ȼ�������������������ɵй���������һ���õ��ƶȰ����Լ�˽Ȩ��ʥ������ȴ��������Щ��ʹ�������Ĺ������������ı���������Լ������棬�÷��ɳ�Ϊ����ʵ�ġ���̨����������Ȩ�������ɵй����������ַ������嵽�����������ǿ�Ʋ�Ǩ�ġ����ӻ������ԣ���ʹ��һ����ʧ��ı걾����Ҳ����������ܡ�
ý��֮���Խ������Ƶض������飬�����ڴ�����������һ��ʱ����������Ҳ�������ԭ���С����ӻ�����ë���ˡ���������������������������������ǽ�������ݶ��϶���18000��������ά���Լ���Ȩ��ʱ������������ý��Ĺ㷺��ע��ͬ�顣��ν��ʱ����Ӣ�ۡ�����һ���˵ļ�ֵ˳Ӧ��ʱ����ֵ������ʱ���ܻ��ߵ�ʱ���ķ���˼��ϡ������ϵ�PSͼƬ����������������ġ����ӻ������ƺ���������ʾ���������ʼ������Ȩ��ʱ���������ӻ�������������
�������еġ����ӻ��������������Ҹ����ܹ���֣����Ҳ���͵Ϯ�����ܡ���Ȩ��������Ч���������ⳡ������Ȩ�Ļ���֮ս�Ѿ���������Щ��ȴ������һֽ��ͣսЭ��������������������װ�ɡ�̹�ˡ�������լ�����𡱡�
2007��12��20�հ��ճ��������´巢����һ��Ұ����Ǩ���¼����������磬������������˾��ϼ�ҷ���ǰ����������ʱ��㽫��������С���淿������סլ���������ٶ�ƽ�ף�����˷��档���������Ҿ�ȫ������������������˾��ϼ������С���淿���⻧Ҳ�ͬ����������������ͼ���Ԫ����ȫ��ѹ�ڷ����
��˾��ϼ�ұ�ǿ����¼���ͬ����һ������Ѱζ��ϸ�ڣ�����Ϥ���﷿�ӱ�ǿ����˾��ϼһ·�ܻؼң������Լұ��ٵķ��ӣ�һ���ε��ڵء�����˵����ʱ��λ��һ�Թۿ�����̫̫Ҳ�ε��ˡ����ܱ��߲�֪����λ���˾���Ϊ�δ������飬������ȷ�ţ����й��˵���Ȩ��δ�õ����ױ���֮ǰ���ڡ����������Ρ��롰���������á������ꡰӢ����һ�������ֺ�����ʱ����ġ����ӻ�����˾��ϼ��������·�ϡ�
������������
��˵������ʤ�����������������Ҹ����ɵı��ԣ�������Ը���ţ������ķ��ɶ��������Ƶı��ԡ�����һ������ʽ�䣬����ľ���ҪΪ����������Ϊ��һЩ����������Ϊ�������������
���ܡ���Ȩ�����������������֮�����罫����Ȩ��Ϊ���ˡ�������������ֱ������ڡ��������桱����ĺ�����ǣ�ʹ�����Ȼ���ֿܵ�Ȩ������Ϯ����������ο���ǣ������й������ǶԷ��ɵĴ��������������µ���ʶ�����ɲ�Ϊ���������ζ����ƣ�����������һ�������������Ƿ��������֮����������������Σ���������������ڷ��ɣ��̶��÷��ɷ��������Ρ����ɻ����Զ��۶��ƶ�����Υ�����ɵ����ܵ��ͷ������ڱ����ϣ���������֮�����Ҹ�Ϊ�ռ�Ŀ�ģ�ȴ�����Ƶġ���ν������������ף�����Ҫ�����η����ڷ��ɣ��÷��ɷ��������������ǿ����й�����Ŭ��Ϊ�������������ǾͿ������й��Ľ�����
�й���Ȩ���������ʶ�빫�����ۣ���һ���̶��ϼ�֤�˽����й��Ŀ��ų̶ȡ���û����1986��ͨ������ͨ�����ͬ�����ȵ��з��ij�̨���ٵ���Щ��������Ȩ�����͡��䡷��������������ע�����ѷ��֣���Ϊ������������Ϊ�ɳ����ġ��б��ϵ��Ҹ������Ѿ���Ϊ���й���ʶ������ȷ�ӳ�˸ĸ↑�ź������ؽ������������Ŀ�����ͬ��Ҳ��ӳ�����ʱ�����������ļ�ֵȡ���뾫��߶ȡ�
�����߳����������������Ƶ��������˵���Ը�����Ȩ�Ŀ϶������ǶԸ����ֵ����崴��Ŀ϶������ִ�����Ŭ��������ζ�Ž����й�����������Ѱ�����������꣬�ڴ��г�һ�գ�����ʱ�䡢�ռ����˵���ά����֤�����Ķ�ͷ���ԣ���ط�����������������ñ�����
��û�����ɲ���˰��
��ǰ�������ӲƲ�Ȩ�ĽǶ���˵����Ȩ��˰Ȩ�DZ���������������Ҫ��ʯ��һ�����ң������ܴӷ�����ȷ������������ڲƲ��ϵĹ�ϵ�����������֮�����Լ�ͻ�ʧȥ����������������ì�ܣ���ʱ���ܽ������������������ij�־��Σ��֮�С�
��������ʱ��������������ʵ�Ը����
���й���͵˰��©˰�ɷ����Ѳ���ʲô���ܡ����ң���ش�������ʵ���ľ߹���Ӱ�졣
2005��6��8�գ���������ִ����������Ъ���ݾ�������ͻϮȫ��17���вݺ�21���й��˾������н���ʮ���й����������40����Ԫ�ֽ𡣾����Ѳ����������Щ�в�ҵ��͵˰����Ϊ����ֻ�ϱ�������֮һ�����룬���ҽ����õ�Ǯ���������������⡣
�����º�Ӣ��������ʱ����������һ��������ţ������ᵽ�����������������˺ܶ��꣬��������й�����һ�ҹ�˾�����ʡ������ܶ���ҵ���б�˽�ң������Ϊ�й��ľ��õ��š��ܶ˾���������ˣ�һ��˰ǰ������ǧ����Ĺ�˾����˰ֻ��һ�ٶ�������ҡ���ͬ�ڿ��ǵĻ���һƪ��Ϊ���й�˰�ģ���ս�����������������¡�����ָ������������й�������˶��ܽ���һЩ��������ҵ�ҡ���˰�Ĺ��¡����й����С�ʮ������ҵ��֮�ķ��ز���ҵ��ȴ����˰��������ĩ����������һ�أ���2003����2005���ϰ��꣬������˰�ֵ���ķ��ز���ҵ��˰�ʾߴ�66�����鴦���永�����1000��Ԫ���ϵķ��ز���ҵ�Ͷ��24�ҡ�
������ʱ����ע�һ����ֵ�������Ȼ���й���˰������������˽����������������й���˰������ȴ�ڽ�����������������ȻԶԶ����GDP��������������л������¶˵����ʮ�塱ʱ�ڣ�2001��2005�꣩���й�˰�����빲��109217��Ԫ���������19��5�������귭��һ���ࡣ�����й���˰���źٷ�ѧ��Ϊ�˱绤˵�����ǵ��ո��ϵ�16��8����2004��GDP�������֣��й�˰���������ǡ������������������Ⲣû����ֹ������˹����־���й���˰����ʹ��ָ������2004��ĵ���λ����2005��ĵ�һλ��
�й��ľ���ѧ�ҳ��ϡ��й����˵�˰�ո�����������������ġ���ý��ͬ����Թ���������������һֱ�����й�������ʽӹ족����������˰���ݳ�Ʒ˰������˰���Ų�˰��רΪ���˱�����˰�֣�������˰�Ĵ�ʩȴƫƫ���Ǹɴ��ס������ꡣ��Ȼ����һ��Ҳ�Dz��ĵĽ�������Զ�������ǰ���й�˰�Ʋ���û����ƽ��Ƹ���Ч�������Ҿ��н�ƶ�ø���������
1935�꣬�����ڡ������Ϸ����ˡ���������롷���������ļ�����11��532ҳ���������ᵽ��������ר�Ҹ����ʵ�һ�����棺���������й���һ������Σ�գ���һ��������������ȫ�������������������������ġ������й������ĸ����������������ط�������ȫ���������Ǿ��������ƶ��ũ��ļ米�ϣ������ʲ��Ľ����ȫû����˰�ĸ�����Խ��Ǯ��Խ���Բ���˰��ԽûǮ����˰Խ�ء�����ȫ����û�еľ���ƽ�������Ĺ�����ʱʱ�̿̿��Ա����ġ����������д�������ҵĵ�һ������Ը���������������������Կ����й���˰�ƶȵ�ת�䡣��Ӧ��˵��ֱ�����գ����ʵ������Ը��δʵ�֡�
������֪��˰�յ�һ����Ҫ���ܾ��ǵ��������ࡣ��ԭ���ǴӸ����������һ�㣬���ڰ���������ײ�Ľ�����ҽ�ơ����ڽ�ͨ�ȿ�֧��һ������ȡ�İ취���۽�����˰�������й������ڲƲ��������������˰������˰���յĶ�����Ҫ�ǹ������ã����Ʋ������Ǹ��˵���Ҫ������Դ������Ǹ����������нϴ�IJ���û�н�˰��
����ѧ��é�����ɴ����Ѷ��ߣ���Ҫֻ�ǹ��ĸ�˰����������1600Ԫ����2000Ԫ��������˰�Ĵ�ͷ�������ˡ���ʵ�ϣ�����˰���и�������˰ֻռ7���������93��Ҳ���Ǵ��ϰ����Ƕ������ġ�ֻ���������ҹ������ܴ���������˰��������֪��������ֱ�Ĺ��ң��Ӱ����Ƕ����˶���˰������������ظ�����˰�ˡ����Ǵӳ����������۸����涼������˰��ֻ�����վ��ϲ���д���������Ǵ�绰���õ罻��ѣ����涼��˰�������վ��϶���д���ס�����é�����������˵�˰���ȸ��˸ߡ���
����û�����ɲ���˰����
�������ᄈ�У���û�����ɲ���˰��������ȫ�෴�����㺬�壺һ�ǹ���û�����ɾܾ���˰����������ڹ����������ԣ�����������˰ʱ��������˵�����յ����ɣ�������ձ���Ծܾ���������˰�գ�������Ե��ǹ����Ȩ�������㺬�忴����������ʵ����Ȩ���������ͳһ��
ǰ�ߣ����ִ���ᣬ���ǽ���������˰�������������ɱ�����������¡�����ÿ���˵�ͷ�������ӱܵģ���˰Ҳһ����һ���ˣ�����������֯�����������Ÿ����������������гɱ��ͼ۸�ġ�
��������ԣ�é����������ָ���ոմӼƻ�����ת�������й�����˰����ʶ��û�н��������������ϰ��������룬������Ҳ�����������Ƶ��뷨����û�а���˰������һ���˲��ɱ�����¡�����а���ƥ���˶��ùھ��˶�Ա�Ľ��������˰������涨�Ѿ�ȡ�������������п�ѧԺԺʿ�Ľ��������˰������Щ�˿�������������˰�������е��������С���������Ȩ���ķ������塪���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