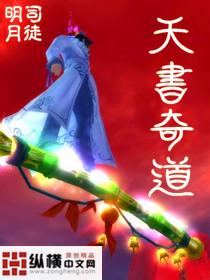后望书-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不妨略作回望。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势衰微,城镇凋蔽,战乱不已。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吕彦直、梁思成、杨延宝等人,都崛起于那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科学现象。
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留学海外归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现代建造技术,又能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国历史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开会评审。交通部南洋大学为交通大学前身,凌鸿勋曾留学美国三年,虽然在美铁路公司工作并在加伦比亚大学学习,但他大抵并没有为学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本领而求学,是继詹天寿之后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设计的铁路1000公路,勘查过的超过4000公路。当时年仅31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40多个设计方案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我们看看吕彦直这位设计大师的简历,就可知道他的方案被选中,绝非偶然。吕彦直于189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自幼喜欢绘画,八岁丧父,九岁随姐姐侨居巴黎,在那里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1928年回国读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之后,他充任美国名建筑师墨菲的助手,参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与此同时,他还对北京明清故宫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亲手绘制了不少故宫建筑图,从而对我国清代古建筑及欧美建筑风格特点都有了全面直接的认识。到1925年投标中山陵时,他已有了七年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其中重要的有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大楼、南京最高法院、东南大学科学馆等等。这位年轻的天才,在中山陵建设未竣工时,即因辛劳而早逝。
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规律。
先说规划。古代中国城市也许没有单独的规划局、城建局这类的政府机构。但多按严格规划建设的。都城、州府和地区的中心城市、边防重镇,更是如此。都城的设计,更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审定,府尹与太守之类,是做不了主的。
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上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规划,建设的“次序”也十分严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后做街道和地面建筑;先造钟鼓楼,寺庙学宫等“公共建筑”,形成城内型制宏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再建店铺民宅。我在山东临淄就考察过2000多年前齐国都城规模宏大的下水道遗存。县、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观、学宫、坛庙——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胜古迹。
再说建筑。
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材料,而是格局、建构、造型和细节表达的内涵。中国地域广大,建筑的材料多样,从来没有排斥过“石构建筑”和新的建筑材料——隋代李春的赵州桥,明代寺院广布的无梁殿,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等等。
“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兼有南北之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看来,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大师已经把大理与丽江古城纳入了视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而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场大地震后,才在危房的抢救中,发现了丽江的惊人之美。丽江古城风貌的保存,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缺乏资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强修旧如旧,这终于为后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丽江印象”。
中国传统城镇的凋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衰落同步。
随之而来的是,在炮火、烟尘和残垣断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信丧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几十年前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所说的,“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着,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这与战争炮火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30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19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疑问与否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和北京一样,中国的许多城市建设并不缺规划,有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制订。我不清楚历届政府作过多少次调整、修改和重新制定。据调查,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规划的“短命”,反映了决策者、制订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规划的思想脉络是什么?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
规划是人制定的,人既可以制定,当然能够修改调整。但在商品经济中,现在修改或调整规划,充满了其他不确定因素,规划部门成了最有权力的行政机关。几位老乡,准备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厂的仓库,双方达成了联合开发的协议。后来到规划部门一看,这片土地在规划图上却画着一个划蓝汪汪的大湖,厂长也不知有此规划。这里根本没有水,只有一条臭水沟从仓库墙外流过,20年了,污染未曾治理。可规划上是水上公园,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现在有专门办批文的公司,花了100万元委托他们,搞到规划部门批文,允许建临时建筑。而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流经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业用地,工业厂区改建小区和商品房,预留的绿地变别墅,其前提都要有规划——而这里的潜规则,都需要花钱。
某一省会城市的规划局长空缺,几个地方官员争着到京城活动跑官,请上头的相关领导或秘书“发话”,有的带了几十万“活动”经费,“同伙”的有一个是我的熟人。在宾馆喝茶的时候,我问,这个职位值那么多钱?他说,与市公安局长差不多吧,可能还更实惠一点,一年挣个200万没问题。我不禁哑然。
有的地方换一届领导就出一个规划。城市规划往往交给设计研究单位,只要拿钱就干活,领导要怎样制定规划就怎样制定。贪大求洋,翻来覆去。一纸规划实施起来有多少约束力?能约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贩和居民的违章建筑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筑工程设计教育的悲哀——“现在是业主教育设计师的年代”。
同样到具体的建筑物设计也是如此。这是给一些官员组成的出国考察团编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参观拍照”。一些单位的官员、公司老板往往拿着出国时拍摄的某个欧式建筑照片,让建筑部门按此模样建造。建设设计单位为了挣到钱,业主单位怎么说,设计人员就怎么画,施工单位当然也就怎么做。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尚跟风、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很难指望业主对建筑文化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还有些专家学者,在洋风劲吹之下,“虽然对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之心理”,他们把这种“鄙弃厌恶”上升和包装成学问,是迟早的事情。
外来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经。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建筑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标,国内建筑设计单位与外国建筑设计单位联合,实际上仅为了给他人搭建一个平台,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仅作陪衬,他们的创造与创新的机会一次次被无情地剥夺。这无形中加剧了一些国内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
在恶劣无序的建筑市场角逐中,为数不多的建筑精英们无暇集中精力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智慧放在谈判桌内外,放在“开拓”市场上。只有获取足够的订单才能求生存,才能过好日子。他们不像教授学者,而更像游走叫卖的商人小贩。建筑师文化思想和独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国当代建筑也是城市的悲哀!
于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终于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二、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争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几乎所有的城镇正经历着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时髦的玻璃幕墙与钢铁的构建,广场喷泉雕塑和绿地……摩天大楼、立交桥,以及城乡间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旧城的废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最常见、最壮丽,也最破败的风景。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
有人说还很低。只有30%~40%。
其实,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70%~80%。北京、上海、天津的绝大数的县已经变成了城区,乡镇变成了街道和社区。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等大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把周围的乡镇都吸为城区,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临潼都吸入了城区。北京、上海取消了农业户口,浙江即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就有水流、路径和方向的问题。
“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从来都是外来闯入者狠毒的一招。重温历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时间的坐标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参照。
两千年的时光依稀。100多年,不算太遥远,半个世纪,更能精确地计算与测距。城市的扩大与停滞,大跃进与大跨越,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一再交错进行的变速成了中国发展的钟摆一般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的理想农村田园风光。
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高潮中,我国中西部大批工矿型城市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靠“上山下乡”缓解失业。止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镇首先精简居民,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了压缩,4年中撤销建制市40多个。对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大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实行了严格控制和限制。
潮涨潮落的中国经济,在文化革命中更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在建国后前30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仅增加了约1。3亿。
——2007年夏天,我到英国访问,从伦敦、剑桥、曼切斯特、爱丁堡和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在20多天的行程中,我再次想到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钢铁的产量。而现在则是GDP。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G D P按照购买力评价实际也已经超过英国。但我们是不是了缺失了什么?——文化、传统,还是城市的历史风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与旅游业的兴起,科学、文化与历史显得如此的重要!
1980年后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城镇净增人口约2。5亿,这还不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富裕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