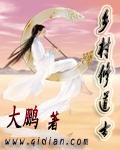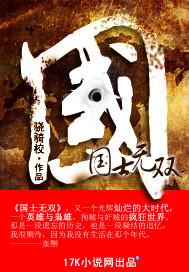大学士-第2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姓考官忙回答道:“赵大人,我二人视力那是极好的,不用担心。”
“那就好,还不快去。”赵尚书挥了挥手。
二人闻言就兴冲冲地跑了出去,一边走还一边小声地议论:“也不知道孙静远这回写的什么精彩文章。”
“不一定是文章,像他这种文才风流的士子,论、述、赋也显不出他的手段。我估计不是诗就是词。”
“或许吧……”
听到这二人的议论,孙应奎面色一沉,对赵鉴说:“大人,这两个呆子实在不象话。身为朝廷命官,不好生维持考场纪律,反去看孙淡的涂鸦,我必上折子弹劾他们。”
赵鉴将脑袋埋见手中的书里,轻轻道:“应奎,这次会试历时九天八夜,呆得久了,别说考生,就算是我等主考官也烦闷得紧。这人的精神若绷得太紧,反容易出鬼。又着他们去吧,只要不出格,乱不了的。”
说完话,就将低头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来,再不多说。
孙应奎摇了摇头:“赵大人,你所读的这本《尚书》,天下间只要是读书人,谁不是倒背如流,读起来又有什么趣味。我看大人读这本书已经两天了,实在是……”
赵鉴还是那副恬淡的表情:“应奎,你在这考场里也呆得不耐烦了吧。这才不过是第一场,后面还有六天,急不来的。”
被赵尚书说破心事,孙应奎倒有些不好意思。
赵鉴微微一笑,孙应奎这个后辈大概是做给事中太久,挑惯了别人的错,性子也急了些,还需要在官场历练个十几年,才能将性子磨圆。如此,才有可能被朝廷大用。
当然,做副主考也的确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
不过,虽然已经是六十多的人了,可赵鉴在这考场里呆了三天,还是有些烦躁。
按照考场纪律,片纸不得进场,即便是考官也不能例外。可为了阅卷方便,贡院里还是满满地放了一架子四书五经。
闲着无聊,赵鉴只能拿起这些书反复看以便打发时间。但可惜,这些教科书,不要说赵鉴,换任何一个读书人,谁不是背得烂熟。看了上句,就知道下一句是什么。
一口馍咀嚼得久了,也没有味道了。
“不过,说起这个孙静远来还真有些才华,不得不让人佩服啊!”孙应奎走到长案之前,提起笔在纸上“唰唰!”地写了起来,一边写一边念:“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安定胡氏改“陆”为“逵”,朱子从之,谓合韵,非也。
《诗》‘仪’字凡十见,皆音牛何反,不得与“逵”为叶,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当作“陆”为是。渐至于陵而止矣,不可以更进,故反而之陆。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而未尝不践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于人君,而其身则与一国之士偕焉而已。
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象也。朱子发曰:“上所往进也,所反亦进也。渐至九五极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杨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极;上九,上卦之极,故皆曰陆。自木自陵,而复至于陆,以退为进也。巽为进退,其说并得之。”
孙应奎写得一手好行草,速度极快,是须臾就将这几百字的文字满满写了一页。
刚开始,赵鉴还在看书,听了两句,他就将头抬了起来:“这是什么?”
孙应奎将笔放下:“孙淡所著的《日知录》的第一卷,下官觉得不错,此人是有才的。”
赵鉴轻轻一笑:“这种老学究一样的文字,读上几十年书,任何人都能写上几句,也不见有甚出奇之处。孙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听说年方十八,居然妄图著述,也不怕出纰漏惹人笑话?”
内心之中,赵尚书觉得这个孙淡很是狂妄,不过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物,不是有德君子。
孙应奎反替孙淡说起好话来:“正如赵大人所说,这种扎实的学问不是普通人能弄的,一时也看不出其中的妙处,还得等孙淡将这卷书完全写完才能知道他的深浅。不过,孙淡的诗词文章还是不错的,先帝和今上都颇为赞赏。”
赵鉴淡淡道:“不过是一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湖星’而已。对了,还有那首什么‘火树银花不夜天’,区区两篇也看不出他的水准。孙淡这个名士的名头,我看有浮夸的成分,当不得真。”上次顺天府乡试,孙淡和毕云、黄锦他们就弄出了那么大事故。时候,孙鹤年他们被杀头,一同给杀被贬被革除功名的人不知犯己。
依赵尚书看来,这个孙淡到过的地方就没什么好事。
自从做了个副主考,他就有些担心,连带着对孙淡也有些腹诽。
孙应奎虽然对赵尚书的话不以为然,可口头却不好反驳,只道:“能写出这种诗句的人,难道还不是大名士?”
“区区两首而已,若孙淡再多写些,有个十来篇,就能看出其水准。”
孙应奎闻言也只能苦笑了,孙淡那一首诗和一首词,已经不让唐人宋儒,这样的句子,寻常读书人一辈子都写不出一句。你赵尚书一开口就是十来篇幅,这不是开玩笑吗?
要不,你赵大人写两首,也不需太好,赶得上孙淡一半就成。
可人家即是高官,又是前辈,孙应奎也不好说什么。
他只能讷讷地卷起那片文章,也懒得给赵鉴看,顺手就扔进了废纸篓里,准备等下叫人拿去烧了。
大堂里安静下来,赵尚书还是捧着那本书看得起劲,可孙应奎猜他的心思一定没放在书本上面,也不知道神游到那个爪洼国去了。
同孙淡一样,孙应奎也觉得考场里的时间实在难混,他提起笔想再写些什么,可心中一思索,却不知道如何落笔。
正在这个时候,一条人影冲了进来。
来的人正是那个木姓同考官,他气喘吁吁,满面都是兴奋,进门就嚷嚷:“看清楚了看清楚,这下我是看得真真儿的,一字不漏。”
赵尚书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孙应奎没发现赵尚书的不满,急忙问:“孙淡写的什么?对了,李大人呢?”
“孙淡刚写完一首词,也没停,在继续写另外东西。李大人舍不得走,让我先过来报信。”木姓官员回答道:“孙淡写的是一首词,绝,真是绝了,不让古人,比肩柳永。”
“比肩柳永?夸大了吧?”孙应奎:“那么说来,我一定得听听,快念。”
木姓官员也顾不得体统,大概是嗓子实在太渴,端起赵尚书面前的那杯茶就牛饮了一口。
赵鉴更是大皱其眉。
木姓官员清了清喉咙,念道: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此句一出口,孙应奎神色就是大变,急道:“等等。”
木姓官员疑惑地问:“孙大人,怎么了?”
孙应奎提起笔:“我记录一下,你继续。”
木姓官员点点头,接着念道: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孙应奎飞快地将这首词录完,突然长笑一声:“好好好,果然好词,有柳永的韵味。”
他目光中有晶莹的光彩在闪烁:“好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好一个孙静远!”
赵鉴哼了一声,旋即淡淡道:“靡靡之音,不堪入耳。”
木姓官员不依了,他亢声道:“赵大人,你说这样的话就有些欺心了。”
第三百五十四章 恰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二)
木姓官员不过是七品官,同二品的赵尚书品级相差十万八千里。若换成清朝,这样的话他是断断不敢说的。可明朝读书人,在政治风气没有败坏之前都有一副铮铮铁骨。
在木姓官员看来,孙淡此人的诗词自然是非常精妙的,就这首《木兰辞》而言,已隐隐将同时代的读书人甩出去半条街。这是客观的事实,不容抹杀。而赵尚书却看不到,反说些什么靡靡之音之类的话,这不是欺心还能是什么?
赵鉴却不生气,就事论事,文学讨论也没有官职之分。他心中虽然不爽,却并不想那官威来压木姓官员,只道:“孙淡也是读书人,学的是圣人之言。看这阕《木兰辞》,说得不过是男女之事,格调上首先不落了下乘,难道还不是靡靡之音?”
木姓官员也急了,扯着嗓子道:“赵大人,词这种东西在宋时本就是市井之人唱着玩的,也谈不上什么格调。当年,有井水之处就有柳永词。写的是市井之事,唱的自然是饮食男女。又不是作道德文章,大人这么说,未免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
赵鉴却回答道:“也不能这么说,词虽然发源于市井,说得也是民间的俗事人情。可苏大学士却也能做出大江东去,辛弃疾也写过醉里挑灯看见。可见,文学一事,在载体上也没什么讲究,关键是看写什么。我看孙淡此人虽然有些才华,却不是个正经人。”
木姓官员有些哑然,若论起口才,他怎么比得上赵尚书这个老官僚。
可他还是不服,正寻思着找话出来反驳,却听到“丁零”一声悠扬而来。
木姓官员和赵鉴同时转头看去,却见孙应奎不知什么时候提起一把裁纸刀在盛水的洗子上一敲,然后悠悠地唱了起来。
二人皆是愕然,仔细一听,正是孙淡刚才所写的那首词。
老实说,孙应奎的嗓子极差,还有五音不全的嫌疑。可他却偏偏唱得摇头晃脑,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
可木姓官员却高兴地一拍手:“好词好曲,孙静远这首《木兰辞》当配上幽怨的洞箫,于月夜之时那一片朦胧之中。让展布唱来才是最佳。”
赵鉴心中突然有些恼怒,这个木姓官员已是个不醒事的书呆子,可孙应奎以前可是个梗直君子,今日怎么如此失态。明明是一首情诗,却说要让展布来唱。展不是什么人,一个戏子,平日间游狎于公卿贵胄之间,一提他的名字,就让人想到一边去。
他咳嗽一声,孙应奎才发觉自己的失态,停了下来。
赵鉴淡淡地说:“好了,孙淡这首《木兰辞》确实有些不错。不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当不得真。由他去吧,你们若没事,不妨随我一同读读书,把心给静下来。”
孙应奎将裁纸刀放了下去,胸口却因激动起伏不停。
那木姓官员却不肯留在这里,一提衣摆:“二位大人,刚才这一耽搁,也不知道孙淡又有什么新作,下官的赶过去看看,就先告辞了。若他新作出来,我立即过来禀告。”
“胡闹,胡闹,赋诗作词又不是写八股,怎么可能说来就来。”见他如此不稳重,赵尚书脸色难看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姓李的官员却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喊:“出来了,出来了。”
再看他的模样,头发也散了,帽子也歪了。
赵尚书一拍桌子喝道:“什么出来了,你现在这样子成什么模样?”
李姓官员突然一声大笑,然后大放悲声,哽咽道:“孙淡又做了一首新诗,苍天,他怎么可能写这么快。难道真得了老天的垂青,将一只梦笔交给了他。老天爷啊,读了一辈子书,我怎么就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说着话,他眼泪不住落下。
“混帐,混帐!”赵尚书还想骂娘,可一听到李姓官员口中念出孙淡所作新诗时,却僵住了。
李姓官员边哭边笑,长声念道:“孙静远这首诗的名字叫《忆徐大将军出塞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理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亿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所谓徐大将军,就是明朝开国时期的大将军徐达。看孙淡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描述徐达大军攻略北平,为大明朝鼎定北方边塞的旧事。
诗词中,自有一股虽百死而不悔,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实际上,三人并不知道孙淡所抄的这首诗的原作者是现代诗人郭沫若。老郭的人品虽然不怎么样,在六七十年代也说过很多违心的话,做过不少错事,甚至没人戏称为郭流氓。可不可否认,在三十年代,郭沫若还是一个热血之人。这首诗写的就是他自己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毅然从日本回国,报效国家报效民族的事情。这诗一出,轰动一时,也激励了不少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因此,但就这首诗而言,郭老对国家个民族还是有功劳的。
而且,郭沫若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虽然以现代诗闻名,可古典格律诗的造诣相当精深,不让古人。
明朝的格律诗本就衰微,当时文坛中人在拟古和反拟古中来回纠缠,争论了百年也没分出一个输赢。而终其大明一朝,好象还真没有一首拿得出手的格律诗。
老郭晚年写过许多不忍猝读的垃圾文字,可这首诗就算是拿到明朝去,也是第一流的。
赵鉴当年在寰壕之乱的时候也带过几天兵,见过血。虽然是文人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