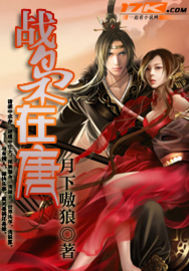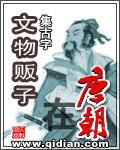文物贩子在唐朝-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腹粗地中锋笔迹,且笔迹使转如意,圆致生动。”
众人听了,其中精于书道地,自然清楚其中关节。更有人以手虚比做书,连表赞同。
卢鸿又指向面前的书卷说:“请诸位细看此书起收之处。虽然做书之人也竭力模仿前人笔法,但此人必然是于桌案上书写。因为桌案上纸张平铺,做书之人手腕与桌面,不如持纸书写之时角度自然。因此入笔收笔时,角度也有所变化,总须以提按分别粗细,难免便显示出笔锋变化,不能如真迹般中锋圆转,不留痕迹。”
众人再细细观看,果然此卷虽然乍看极似古人笔法,但出入笔锋,总需略见扭转提按之处,比之真迹自然变化,确是不同。
卢鸿悠然说:“综上纸、墨、笔法破绽可知,此卷应为书道高手,拟照大令书迹所造赝品,又经伪饰,故颇为精彩。据小可胡乱猜想,踞今不过数十年至上百年的时间。只是究竟何方高手,有此等手段,就不得而知了。”
卢鸿话音方落,便听李泰鼓掌赞道:“精采之至!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日方知卢公子才占八斗,确是名至实归。”
众人到了此时,也不由哄然称是。本来众人均认此卷为毫无疑问的真迹,此时听卢鸿一说,却是处处破绽,对卢鸿的识见,只能说个“服”字。
卢鸿谦逊了几句,李泰又说:“今日本王虽然误收赝品,是为一失;但能闻卢公子高见,亦为一得。得失相较,怕是所得更多啊!今日佳会,对酒当歌,鉴古论艺,实为平生快事。卢公子适才言道,雅好诗词;又见书道见识,超绝无伦。不知泰等可有幸,一观公子诗书绝艺,以记今日之胜事?”
卢鸿看着李泰目光中的含义,知道今日自己表现太过,惹起了李泰爱才之念,招揽之心,仍是未绝。只得叹了一口气说:“魏王有令,敢不从命。只是乡词曲,疏狂之性,只怕难登大雅之堂。”
李泰闻言大喜,道:“能得卢公子赐观大作,实乃三生有幸。”说罢,忙命侍女奉上文房四宝。
卢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适才观看魏王所藏佳作,一时心动,不愿于方寸纸上做寸书小字,却要借白壁一用,放浪之处,还望魏王休怪。”说罢,右手提笔,饱蘸墨汁,双眼斜睨身边雪白的墙壁,微做沉吟。
众人一听,这卢鸿居然是要在壁上作书,一时颇为惊奇。
唐时人每有狂浪之时,尤其在酒坊肆之处,酒酣耳热之时,往往将诗作书法,题于壁上。若有佳作,往往店家酒坊,也会引以为荣,宝藏珍护。只是此地乃是魏王府上大厅,卢鸿要在此题壁留诗,也确实有些放肆了。
卢鸿不管众人议论纷纷,双目微闭,左手在壁上轻轻抚摸。片刻之后,忽然一口将胸中酒气吐出,右手持笔直落壁间。只见他行笔如急风骤雨,时而重挫,时而轻提,有时连绵数字,竟然一笔直下;有时又跳跃翻转,笔断而意连。众人只见他以腕运笔,将一只笔运得如同有了生命一般,那或枯或润、或疾或迟地笔迹便吐露其下,一霎时墨迹纵横,云烟满壁。
待得最后卢鸿重重将笔落下,写完最后一字,仿佛全身力气也随之而去,竟然略现疲态。
众人定睛再看,壁上写满草书大字,却是一首《将进酒》:
琉璃钟,
琥珀浓。
小槽滴酒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
罗帏绣幕围春风。
吹龙笛,
击鼓;
皓齿歌,
细腰舞。
况是青春日将暮,
桃花乱落零如雨。
劝君终日酪酊醉,
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卢鸿轻吁一口气,右手毛笔随意掷去。左手取过酒杯,将杯中剩酒一口饮下,淡笑道:“魏王见笑了。卢鸿酒后狂浪,还望恕罪。此时不胜酒力,恐有失态,便即告辞。”
第五卷 名动长安
第十三章 修书工作会议
鸿回到卢承庆府上后,毫不停留,直到卢承庆书房中明今日魏王宴上诸事。
卢承庆沉吟许久,这才缓缓地说:“此事虽然暂时对你或有不利,但长久看来,未必便是坏事。反倒是你若投于魏王门下,对你日后发展,颇多不利之处。魏王虽然看来声望过人,贤名远播,但毕竟不是太子。虽有圣上宠爱,但储君废立,自古以来便是国之大事,帝基根本。只要当今太子没有太过份的举动,只怕也是白费心机。你既然欲游于仕林外,还是及早抽身的好。依老夫之见,不若自此便谢绝一切宴饮之事,搬到孔老夫子府上,专心修书才是。”
卢鸿听了,也觉得这几日周旋于酒林歌舞,出入鉴古诗词之会,甚是厌烦。又免不了应付来应付去,总也没个头的。也点头说:“侄儿也有此感,只是搬出府之后,朝夕少了叔父大人指点教诲,又不免思念叔婶。”
卢承庆笑着说:“你搬出去,你那婶婶自然也是要念叨的,修儿更是少不得喊着舍不得你了。只是大事为重,何况搬到孔府,只要得闲时,随时走动,有何妨碍。”
是日府中家宴,为卢鸿践行。卢修闻知卢鸿要搬走了,颇是不舍。但父亲既然决定了,又知道卢鸿身任重负,也不敢多说,只是嘱咐卢鸿有空常回家来看看。卢承庆夫人也是很喜欢卢鸿,这一段卢鸿名声大著。居然多有权贵看中卢鸿,便有那贵妇跑到卢承庆府中,与卢夫人探听卢鸿生辰多少,亲事可订。其实卢鸿已然订亲阳郑氏,所知之人也不少。但长安权贵本自矜贵,原来对卢鸿多并不在意。此次突然间见卢鸿名动长安,临时抱佛脚,也是闹了些笑话。
次日。卢鸿便收拾行装。带了洗砚。搬到了孔颖达府上,准备修书事宜。至于再有宴请集会之事,一律便都推了去。
孔颖达见卢鸿这么快就忙完了私事,搬来准备修书,也是颇为惊讶。这些日子卢鸿之名,轰动长安。举凡短柱新诗、鉴古博今的事迹,大受喜欢风雅流韵地长安人的追捧。更加上卢鸿年少英俊。学名本著,一时更是成了年青人及闺阁少女们最崇拜的人物。
见卢鸿这么快就从俗事中脱身出来,孔颖达颇为欣慰。府中为卢鸿准备的客房早就收拾好了,又命人再简单洒扫一下,卢鸿行李不多,很快就安置下来。
此时孔颖达身为国子祭酒,但因又重修《五经正义》一事,国子监中事务。除非重大仪典之外。均不再过问。就连担任太子右庶子一职,也得许可,由赵弘智接任。脱身开始专心修书。孔颖达这座府邸本是朝中所赐,规模不甚大,分为前后两院。后院乃是家人居住之所,前院就是办公的所在。正堂左右分为书房及会客室,平时与众人商议事务,便均在书房之内。前院两侧偏房,便是同事修书的场所,分别诸经,各有房间。
此时修书之事方始启动,诸人也都结束了当前事务,逐次来孔府报道,准备开始重新审订《五经正义》。能参与此事者,均是博学名儒,除了上次卢鸿见过的颜师古、马嘉运之外,更有司马才章、王恭、王德昭、朱子奢、谷那律等闻名已久的前辈高儒。
待得众人均已到全,孔颖达便在自己书房中,主持召开了再次审订《五经正义》地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上先是宣读了当今圣上关于重新审订《五经正义》工作地旨意通知,学习了朝庭有关审书工作地指示精神,回顾了第一版正义发行以来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审书工作中存在的热点及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会上国子祭酒孔颖达同志做了发言。孔祭酒指出,审书工作是圣上交办的一件重要工作,是关系到大唐文化事业发展、影响到科举工作举办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大唐社会和谐、文明昌盛地智力准备和精神引导。因此,审书工作一定要在紧紧团结在当今圣上的周围,在朝庭的指导和支持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下定决定、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众志成城的大无畏精神,优质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此次审书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大唐建设贡献力量。
孔颖达修养本深,学问功夫扎实,这一番讲话下来,引经据典,有理有节,起承转合,俱有章法,直说了有一个多时辰。在座诸人洗耳恭听,还有数人手持新版线装笔记本,边听边记,一场会下来,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楷,另人不由佩服这记录功夫。
只是待到讨论之时,却是难有进展。孔颖达为人比较随意,会上更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因此众人都也各抒己见。原来此次
将书回炉重修,主要是因为存在几点问题,在使用中处。
一是《五经正义》经义庞杂,规模过大。本来朝庭编纂《正义》,是为科举取士制订统一的经解教材和课试标准。因为当时不仅学分南北,更有各姓“师法”、“家法”,各不相同,义理混杂,众说纷纭。前朝隋代首开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因没有标准经义,众博士几乎无法评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但孔颖达主编的这部《五经正义》虽然基本统一了经义,但是引用太甚,连篇累牍,足有170余卷。若真以此为教科书,不说出版之事成本过高,工程浩大,就说是教学引用,也是难为人。因此朝庭便有意精简篇幅,去芜存精,以利流传。
二是《五经正义》博采众家,广纳诸说,颇有矛盾纰漏之处。初次修书时,乃是在众多地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注释作为标准,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其他编修之人负责具体注疏,凡有矛盾争议之处,再由孔颖达综合诸说定夺,以为终论。如《正义》中《易》采用王弼注,《诗》用毛传郑笺等,其他诸经,也均以前人流传较广地疏义注本为宗,整理成书。虽然此法成书迅速,易于采编,但诸经之间经义也有难免互悖之处。加之成书太快,难免存在疏漏谬误,故需要重新考订。
三是《五经正义》一些词句,因采前朝旧义,有失朝庭体统。如在《尚书。“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旧时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详查的缘故。这些自然是须得一一删正,以明正朔。
但如此一一论来,重审《正义》一事,委实难以下手。尤其与第一次修书不同,具体摘录工作不是非常多,最主要地是对已经存在的经义进行审订重考。这样一来主要工作,怕都要集中在孔颖达这主编的头上。无怪乎孔颖达觉得精力不足,要召卢鸿进京相辅了。
众人讨论了半天,总是觉得难有着手处。不管是精简、统一以及删正,首要便是主编之人,拿出一个最基本的立论标准来,为众人接受后,才能以此为据,或删或修,不然便无处着手。但前时之所以广采众家,便是因为难以一家之说为贯。此时若要重订,却是要推倒重来一般。那词句间的修订,倒尚在其次。
此时天气渐热,孔颖达这书房不算宽敞,屋内挤着众人本就狭窄,甚是闷热。众人说得热烈,更有几人满头是汗,也未争出个所以然来。
卢鸿因是初次参加会议,虽然孔颖达将他向众人做了介绍,互相之间也都早有闻名,表现很是亲近,但他毕竟是孔颖达的学生身份。何况初来乍到,不便多言,就一直未曾发言。
孔颖达见卢鸿一直站在自己身后,未出声讨论,有心要他参与进来,便说道:“卢鸿,虽然你是我弟子,但日后相辅修书,也免不了多作参与。此事你有何见解,不妨也说来听听。”
众人听了此言,不由一齐将目光投向肃立在孔颖达身后的卢鸿身上。此间众人,虽然多是首次见到卢鸿,不过在座的均是经学大家,对卢鸿在玄坛首倡气学、范阳经辩新解老子等事都知之甚详。更有数人对气学颇为推崇,因此对卢鸿,都不敢以后辈小视于他。见孔颖达要卢鸿发言,均静听卢鸿有何高见。
卢鸿也不做态,面带微笑说:“学生倒是有个提议。”
“哦?”孔颖达说:“有何提议,讲来便是。”
卢鸿说:“学生想这修书也不是一时之事,总要反复讨论,细为推敲才好。看老师这书房甚是狭仄,诸位先生都是闷热难当。此时院内松荫如盖,清风习习,更有石凳生凉,藤萝旁绕。何不移座院中,学生为诸位先生烹茶以奉,平心静气,再论修书之事,或者更有灵机,豁然开朗?”
众人听了卢鸿这提议居然是这般,不由尽皆微笑。唐时官府中,其实不似后世般严肃沉重,同僚间饮茶闲谈也是常有的事。那颜师古先就大笑说:“我们这一群老夫子,还不如一个后生晚辈心态平和了。嗯,如此议论公事,不妨正务,却多份闲情雅致,甚得我心。冲远兄你看如何?”
孔颖达笑着说:“我这学生,不管何事,总是要弄些闲散之趣来。好,便依众议。卢鸿,你便准备茶具,我等只静等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