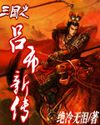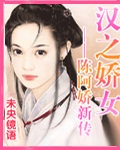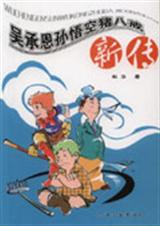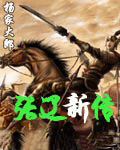�����´�-��7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ȫ����Ȩ���ɴ˱�����˴����ط�����¹ٵľ��ס������ۼ��������м䣬Ŭ������ƽ�⡣���꣬�¹����õĵܷܵ��������������߽��䴦���������۵������������ã���������Ϊ˾��Уξ���ñ������Ӽ��������Ϋ��Ȼ¹ٵı�����ѹ���գ��������۵���նɱ��ʮ�ˡ��������Ϋ������ۿ��ߣ����۷�������������Ϊ����������Щ����˵���������۲���һζ̻���¹٣����������ֻ����Ϊ��û���˲��ֲƲ�����Ҫ�öԷ������أ���������æ��������Ҳ�����ܳɹ�����ʵ���ż����˾�Գ�Ҳֻ�DZ������ͷ�����������۶��ѡ��ż����ֻ���ܵԳ�֮��������û���˺����IJƲ������º��������ر���������
�ż�Ӱ��֮���Ի���˹㷺����Զ��ԭ�����ż��ƻ������IJƲ������һ�ɱ�˺����ļ��ˣ���ڱ����Ӱ���Ҫ���ء������顤�����д���ֻ�Ǽ��ἰ��ɽ���ż�ɱ���̺���ĸ���������͡����ۼ͡��Դ˰��ļ��رȽ���ϸ����ڴ������£�
�ż��ڽֵ�������������ĸ��һ�У��Է�������·���ż��ŭ�����˽�������ĸ����Ҿ졢���۰�����˵���ɱ�����ֵ����˺�����ɽ���������صķ��ᣬ���ֻ��DZ�ӡ��������ű�����´�گ�飬�����ż�͢ξ�����ܵ��顣����ʱ�ż��Ѿ����ߣ����кܶ�Գ�͢�����Ĺ�Ա�Ͱ��հ��б������ٸ�����ץ�������ڱӻ��ż�����У������ᡢҲ��������һλ������ʱ��16����Ŀ��ڡ��������ż��ڿ��ڵ��˵İ����£���Խ���ǣ�Ͷ���ʱ���ȥ�ˡ�
����ż�����ȷ�硶�͡���˵����ô������������ȥ�����������ˡ�����������ż�������һ��ȥ͢ξ������ѯ����ô����ֹһ�����������ܻ����������������⣬�������������������������ˡ�������һ�ӣ������˵������ˡ������۵�Ϊ������ʼ��������������諡���襡������ʸ�Ļ¹ٶ����Աܻ�������Ҳ���ܹ��ϳͣ������ܱ��ر�̻���������������Ļ����ߵģ��϶������ż���ɱ�����ļ��ˣ������ż����ߺ�һֱ���ܱ�ץס������Ȼ�������ͨ����������ǧ��ɹ��ƺӣ������ڶ�����Ҫ������Խ����ȥͶ���й������ɣ��ⷴӳ�˵ط����ֺ���������Ƕ�ô���ҵط��Զ�����Ȩ�������������۹��ƶȡ���ˣ����۲Ÿе��б�Ҫ����һ��ּ���������Ŷ���������˶���������˶������־ͽС�����������˼�ǡ���ֹ�ᵳӪ˽���˵��١���ͬʱ��������������������Ѳع��ż����Ա���������������˴�����������ȴ�õ������⡣
��Ϊ�¹٣����������ڴ�Ħ�ʵ۵���˼����Ԫ166���^����ָʹ�ųɵĵ������ޣ����͡�������˳�������飬˵���ߡ����ܵȹ�Ա��̫ѧ���ᵳ���̰���͢���ܻ����ס����ۼ��ˣ���Ȼ��ϲ��������ָʹͬ���첢���飬˵�ż���ɽ������������24�����������Ϊ��ν�ġ��˿��������˹ˡ������˼��������磬����ʯ�����������ű���ŭ����گ������24�ˣ���ֻץ�������������������˶�ʧ���ˡ������飬���������dz�����ξ������ͬ���ѧ������������̫ξ��ެ�Ĺ�������������Խ��Խ��ȷʵ�������������Ĺ�ϵһ�����У������������ξ�����ʱ�����������ӡ����������ӡ�֮һ���Ӳ�Զǧ��ӳ���ǰȥͶ�����������������
��Ԫ166��ף���������گ���������˾��Уξ���ߡ�̫�Ͷ��ܵ����������ˣ��ԡ������������������൳�����ż�һ�����ߣ���͢�����ؽ��ã������ջ���û��ȫ��ץס��������ί���г��������������������ߡ����ܵȱ����ĵ��ˣ����յ����ʼ�¼��Ҫ����������������ǩ�֣����ܷ�������Ч����
��ʱ�����������˵�����������˭����ȻҲû�ж��ۡ���һ�Σ����ʵġ����顷����ʧ��������ì�ܡ������顤Т���ۼ͡�˵����Ԫ166�����£�̫ξ��ެ����ְ�����£���»ѫ�ܾ���̫ξ��ʮ���£������˶���ʼ������һ����������Ѷ���˵�̫ξӦ�����ܾ��������dz�ެ���������顤��ެ�д�����ȴ˵�����ߵȵ��˱���֮��̫ξ��ެ�ϱ�Ȱ�ɣ��������ְ�������顤�����д�������˵����ެ��Ϊ̫ξ����Ҫ���������λ����һ������������Ѷ���˵ļ�¼��ǩ�֡�����˾����������顷���ˣ���Ȼһͷ��ˮ�����������ġ�����ͨ�����������д�����˶��������ĸ��¡�
���ԣ����ǻ��Dz��š��͡���˵���ɡ������˶�ʼ�ڹ�Ԫ166����£���ެ��̫ξְ����δ�������۸������ެ��Ӧ��������λ��������˾ͽ���㡢˾����ïһ������������Ѷ���˵ļ�¼��ǩ�֣�����������ϣ�������ϱ�Ϊ����˵�顣�����۲�Ϊ������������ߡ����ܵȵ��˹ؽ��������������������������
�����˶���ìͷ��ֱ��ָ����ȫ�й�����������֪ʶ���ӣ����Ҳ�ر�Ϊ��ʱ�ͺ�����֪ʶ����ڸ���������ԡ�ʿ����ԾӵĶ���֪ʶ������˵�������۹��ӵ����˶���ʼ������ȫ����ֵ�����ǵ�ά���ˡ�
���ǣ�ʿ���ӵ����д��ʷ����Ȩ��ȴ�����ܹ������ı���ҵ����ˡ������ܹ�������ʷ����ģ���������Щ��ʿ�����ӵľ��ˡ����ڵ����˶�ǰ����ȴ�����վ�ں�������¹�һ�ߣ���;�����ʿ�������з������ն�����������ѹ�����ˡ�
���й��Ŵ����е���һ���������۵��ֺš����������˳�͢������������Ĺٷ����ۡ��������ɾ��Բ��Ƕ��֡����������顤�ַ��⡷�����ٽ���ԶԻ�����˾�����Ի�����������Ի�����������۵�һ������ʵ���������µ�һ����Ҳ���书�պյ�һ�����������������϶����ģ������Ⱥ�ʿ���ĵ����˶���
��ǰ������������������֮��Ϊ��Ťת���������ս�˥�ǵĹ��ƣ����š��ʡ��á��塱��������Ҫ��������Ԭ����ȿ���Ԫѫ�ĺ����������»�ĺ��ų�Ա�������ش����������˲š��ھ�����������ۡ������Ϲ���������Ψ�Ŷ���Ψ�ף����ó���¢��������Ȩ�ĵˡ����������Ƚ��ų�Ա��ת������¼����٣���������Ҫ�����������ݵ���λ���죺�ʸ��桢��ۼ�����G���ʸ�������������ۼ��Ȼ�������G�ּ��������Ժϳơ���������������ۼ�Ͷ��G���������Ĺ�����������̨֮������û��һζ�ų��������������á��������������������������������ڶ�����ս��ʤ�ٰܶ࣬�ر���Ǽ�˶�κ�ɨ���ݣ��Ӽ����ݺ����ݣ�����˾���ƻ�����������������Ŭ���£������ܿ�Ťת�������ı������棬�������ڶ��������壬�ո��˴�Ƭ������
��Ԫ166�꣬�ʱ��˵Ĺ��ƽ���˥������Ǽ�Ѿ������������ǼҲ½��Ͷ���������۹��Ĺ����������´��������������£�����ӭ����ǰ��δ�е�Զ�����͡������������ص�ʹ�š������ء���Ȼ�ǡ������ᡱ��Antonius���ĺ������������˴��ġ����������ء�����Ϊ�����ʵ����ɡ������𡤰����ᣨMarcusAureliusAntonius����Ԫ161��180����λ�������˲�ѧ��ţ��ųơ���ѧ�һʵۡ����Զ����Ļ�����Ũ�����Ȥ���������й���Dzʹ���ƺ�������֡����ǣ���ʱ���к�����Ա�������ʹ���Ǽ�ð�ģ���Ϊ�ں����й���������������ԡ����ڡ����ƣ�����Щʹ�߲�δ����ʲôϡ����ص���Ʒ����������佲���û�У�ֻ��������Ϭ�ǡ���裵ȶ����ǵ��ز��������ݻ��ɵ��ǣ����ʹ��֪�������������ʵ��ա������ᡱ����ֵ��ע����ǣ������Ǿ������Ǻ������������й��ģ�˵������½��˿��֮·��ʱ��Ȼ��ͨ����ǰ�����������������������ܾ���������־����Ҳ�Ѽ����˴Ӻ캣�������ɹ�ӡ������Ϻ������й��Ϸ��ĺ��ߡ������������ⶼ����˵�Ƕ���������ʷ�ϵĿ�ǰʢ�£����������ɡ���������й�����Ҫ��
�������ڹ�Ԫ166������й������dz���żȻ���ں����ƪ���У����ǽ��ῴ�������ν�ġ�����ʹ�š������й�����ʷ����������Ҳ���ᷢ�֣�������ʵ���й�������һ���������߱��˶�ʼ��δ����ϡ����Ʒ����������صġ��˶������ӡ���������ɳ�����С�����ͻ���ҵ�����ϸ���֮·�Ķ����۹���Ȼ˥����
���ߴ���ʹ��֮��Ԫ167�����£���Ǽ�ֿ�ʼ�����ԡ�ʱ�λ���ū���ɽ�����ۼ��Dz���µ���Ա�����������˺Ͷ���·���������˵о���ͬ�£����һ֧��Ǽ���䡪������ǼΧ����������ʱ�λ�ǼУξ�Ķ��Gǧ���Ԯ���磬һ��ȫ�ߵо������ˣ���Ǽ���䱻��ȫƽ�����ڳ�����60����֮��Ǽս���������˼������������ס�
���ա���֮���£��������֡������ͳ�������������۵�ȷ�dzɹ��ľ������ر�������֮ǰ��֮��ļ�λ�ʵ���ȣ��Եø���ͻ������������ʱ�ڣ����·����˳�������������٣�����������ʧ������Ѹ�ٻָ����˿�ƽ���������۹����������������ϵ�����������ӡ�ȵ�ңԶ�Ĺ��������빱�������۹�ٲȻ������֮�ࡣ����һ���Ƕ����˿�����ʱ�ڣ���Ԫ157��ȫ���ڼ��˿�56486856�ˣ��������ػ��ں��������壬ʵ���Ͽ��ܽӽ�7ǧ��Ϊ������������֮�������ʱ�ڵĻ��ڶ��ֱ࣬������ʱ�ڲű�������
���ǣ������۲�������ʿ������⣬���Dz���ָ�ۻ����ȣ��������ڽ̣�������ֱ��֪ʶ���ӡ�ʵ���ϣ��뻸��������ۡ�������ۺͺ�������Щ��ν�ġ�������Ҳ�ͻ���һ���������м���������ȫ��֪ʶ���Ӷ����������ʼ���۵�ʱ�����������ڸ��������ܳ����κ�һλ�ܹ���ʿ�������ľ�������������Ը�Ѵ���Ȩ�������ˡ�
���ź�Ǽս���Ľڽ�ʤ����������Ҳ������������á�����̫ξ��ެ֮�⣬��͢��������Ϊ����˵���ߡ����ڴ�ʱ����Ϣ�س��ֱ���Ȼ������������
��ʿ���������λ�ֱ뱾����ʲô���ˡ�������̫ѧ�����䣬���̩������������Т���������Ͽ�������Ϣ�س������ú���ᯕy��Ϊ���ż��������˲���Ϊ���˼��������ڴ����ڼ���ɱ�����۳��ҵ�������ȫ�Ҷ�����ڣ��ͨ�������������Ͽ��С������ط���Ա��������������أ�ֻ�мֱ벻�Ͻ��ɣ�˵��������ҪЮ���ϣ���ɱ�����Է�������ֲ��ҵ������Σ��Ĵ��������������ѣ����Ǵ��ɷ�����Ϊ�س�����ȥ��������������ˣ��ѵ�����Ҫ���������������𣿡�
����˵���ߡ����ܵ����������ֱ�ȴ����ס�ˣ�����ǰ����������������נ�ͳ���Уξ��䡣��נ��������������������������������������ǻ��۵���������������̸��������飬һ�����̴���Ǽ�ˡ���������Ĺ��������ѻ���Ӧ�ô������£�һ��Ϊ������ԩ�������Լ����岻�ã�ϣ����������Уξ�ͻ�����ӡ緣����ݻؼҡ�
ͬʱ��������������١����г���������̬��Ҳ�����˶�ҡ������������Ѷ�������ĵ��˾�Ȼû��һ��������ģ������ߡ����ܵ�����˵������ܶ�¹��ӵܹ�ϵ���У�����������Ϊ�ѡ���������飬���ɴ��Ҳ�������࣬�뻸���´����
��Ԫ167�����¸����գ������������������⣬�ͷŵ��ˡ���һ�ε����˶��ڳ�����10����֮����ʱ��һ���䣬������Ҳ½�����س�͢���١�������˶��У��������ż�ᯕy��������ֱ���й����⣬�����˱������������ǻص����������ͬ�½����磬��ɫ�˵�Զ���ϰ�����ӭ�ӣ��ۼ������������ǧ������������صĽ�ͨ���������˷�������龰����̾˵���������ⲻ�Ǽ����ҵ�����𣿡�
��һ�ε����˶�����֮ʱ����Ϊ��������Ԭ��Ӧ��ǡ�ù�����ʢ���ڴ�ǰ����������������Ҫ�£���һ����Ȣ�����ӣ��ڶ���������ĸ��ȥ������Ϊĸ��ȥ��������Ԭ�ܰ��չٳ��Ĺ�أ���ȥ�������һְ���ؼ������ɥ��
��ǰ���У������Ѿ����۹�Ԭ���״ν���ʱ���Ԭ����λ���ӵ��������⣬�����ǣ�Ԭ��Ȣ���ڹ�Ԫ170��֮ǰ��Ԭ̷�����ڹ�Ԫ171����ǰ��Ԭ�������ڹ�Ԫ172����ǰ����Ԭ�г����ڹ�Ԫ172���Ժ�
Ԭ�ܵ�ĸ������ʱȥ����ʷ�����ġ����ǣ�Ԭ�ܵ���ɥȴʮ���������ݡ�����־������֮ע���ʸ��ס���ʿ�����ļ��أ�Ԭ����Ԭ���ֵ�ɥĸʱ�������ڼ������ϣ��ܲ١������������˻��ᡣ�ܲټ��������ʢ���������Ķ�����˵�������¼������ң�Ϊ������һ���������ֵ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