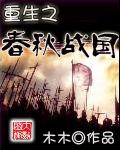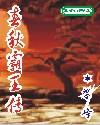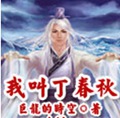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相信。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多。如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我主观唯心论总是太多,学生提意见的方向总是对的,我只有彻底革自己又臭又脏的旧命。……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中文系宗派我应负全责,别人依仗我他才敢搞的。在九三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秦瓒争九三主委我和他一唱一和,我是赞成他。反右中,对秦瓒我做了逃兵(未揭批秦瓒)。……我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都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先生酷爱京剧)……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我对教学是庸俗观点,我说你们(共产党)既要古典文学,就要借重我,这与右派份子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有何区别。其实我掌握的材料也只一点点,向党讨价还价这种想法卑劣不堪。我以不备课自豪,我备了40年的课嘛?后来备了,目的是讲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我是为自己教书,我没有管着学生。讲浅了怕人笑我,我只面对自己完全是政治立场观点不对。我对社会主义教育不热爱。我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丝毫不知道,看一点也是断章取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破是破了,立什么呢!”
6月11日晚,在党委研究运动的会上,李书成书记作了十点讲话,其中第七点指出:“要掌握分寸,思想行动上必须一致,挑出重点必须有代表性……刘文典必须反复批判。”6月15日党委会上,李书成书记在安排各系各部门作运动小结中谈道:“重点批判,国宝专权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思想,威风打垮了,刘文典、方国瑜两个堡垒垮了。”到此,对刘文典先生的批判总算告一段落。
“堡垒”攻克下来了,刘文典的生命随之也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14日深夜先生在家突感头痛,不一会儿昏迷不省人事,云大校医及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及时赶到,诊断先生系脑溢血抢救无效,于7月15日下午5时过世。张德光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杨副校长通知与刘尧民研究刘文典后事。刘太太坚持不火化,要装棺运回安徽去,狐死首丘恐办不到。”“狐死首丘”一语,意为远出的狐狸,临死时还面朝故土首丘。一代国学大师忽然逝去,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中,头几天云大党委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恰当。既没有发讣告,也没作追悼会安排。直到全国政协接先生夫人张秋华女士电报后,给云南大学发来唁电对先生逝世表示慰问(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云大党委才急忙和省政协、省九三学社云南分社筹委会(先生为筹委会委员)共同协商,于7月23日由三家联合在云大大礼堂为先生举办追悼会。追悼会自始至终简单冷清,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到会者仅100多人。云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未参加,仅派杨黎原副校长到追悼会场。中文系未送花圈,系主任也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白小松先生(曾任云南大学教授)致简短悼词后草草收场。
1960年6月22日张为骐教授谈及此事还愤愤不平地对张德光说:“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叔雅先生追悼会,中文系居然不送花圈,历史系送了花圈,因为你是系主任嘛。”1962年8月24日,张德光与周新民(民盟元老,代表民盟中央到民盟云南省委视察)在昆明白鱼口疗养院散步时,周新民谈道:“你知道刘文典在云大的情况吗?交心运动对他批判过火,那么大年纪,而且又有病也不照顾一下。死了对他很冷淡,他爱人回到安徽生活有困难,这些事传出去很不好。其实刘文典这个人很有风格,在安徽时蒋介石拍桌子骂他,他也拍桌子,这就很难得……”刘文典先生之独子刘平章先生与本文作者可称世交兄弟。一次平章先生悲愤地对我说:“老弟,父亲去世我从重庆工学院(先生为该院教师)赶回来办理父亲丧事才知,在4月份一次批判会后父亲在回家路上吐了几口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污,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徐铸成当卧底
作者:贺越明 字数:4434
在1957年夏季展开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撰写、改定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先后以《人民日报》“本报编辑部”和“社论”的名义发表,时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在劫难逃,再三检讨仍未过关,很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报社职务撤掉,全国人大代表除名,随后与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文教界人士一起,先去郊县农村劳动,后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束后安排至出版局工作。因他这一阶段多次汇报学习和改造的心得,被视为进步明显,于1959年9月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是那场政治运动中落难后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之一。可见,比起其他同入另册而尚未解脱者,他获得了较多的肯定和信任。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又使他此后几年除了日常的图书审读之外,还承担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前后经过,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右派”问题改正后所写的自传以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从未有一语涉及。若非北京三联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了《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在那些文革时期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中时现时隐,他的这一独特经历很可能湮没无闻。
“运动档案汇编”中最早披露这项特殊工作的文字,是徐铸成写于1968年2月7日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首先说明他在“反右”前来往较密切的友人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等人,随即陈述了他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江华指派去做其中几位“思想工作”的经过:“60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本来,徐铸成在“反右”以后自惭形秽,愧见故人,除了沈志远之外,与那些朋友大都不再来往,但因为江华布置了这项工作,只好带着任务登门拜访。
对于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江华有具体的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针对徐铸成产生“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的顾虑,江华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做工作。”徐铸成奉派去“量量温度”,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如何开始第一步呢?江华问徐铸成“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徐如上所述举出李平心等人,于是他就叫徐先去看李。徐铸成写道:“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
据另一篇写于1969年1月22日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披露,或许是考虑到徐铸成初次从事这类工作,江华作了详细的指点:“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于是,“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是记者出身,在上门访谈过后以对话体详细记录谈话内容,自属驾轻就熟之事,而史学家李平心极可能在茫然不觉中,被统战部通过老友掌握了思想动向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看法。
徐铸成在文革期间的几次交代中说,按照江华的要求和布置,他以这种目的和方式接触的对象,还有翻译家傅东华、语言学家金兆梓、历史学家王造时和画家刘海粟等,而这些著名文化人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他写道:“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江华没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再接触过。”之所以写下这些交代,徐铸成是为了辩白在“右派”摘帽后与这些朋友或熟人的来往纯系奉统战部干部之命,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否则,他们这些“文革”时进入“牛鬼蛇神”另册中人,如若被革命群众调查发现曾经相互来往的行迹,很容易就被扣上“私下串联”和“图谋不轨”的罪名。
此外,徐铸成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参加上海市政协学习时,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的霍锡祥在一个小组。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中写道:“江华有时也派我了解他对时事问题的看法,我和他谈后都写了书面汇报。”显然,解放后响应中共号召从香港回来的这位市政协委员,仍然是统战部门非常关注的对象。
徐铸成的这项特殊工作,对象不光是上海本地其所熟悉的高级知识分子,《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还说:“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浦熙修是著名女记者,原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反右”中被毛泽东的宏文讥刺为连接罗隆基与上海《文汇报》编辑部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宋云彬是文史学者,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与徐铸成属好友。
不过,江华向徐铸成交办的特殊工作并非都能顺利完成。比如,《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也写了吃闭门羹的事例:“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还有一位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徐铸成在另一篇《交代与一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交往关系》中说,与他“过去气味相投,常在一起应酬喝酒。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好而已。统战部领导60年前后曾希望我做些他的工作,我说明困难,没有做”。有些什么困难呢?徐的交代材料没有说明,但似乎不难揣测。赵超构在“反右”期间检讨一番即过了关,不但没有被划成“右派”,而且在1957年6月和9月、1958年1月三次获得毛泽东的小范围接见,晤谈甚洽。令人不解的是,对被毛泽东称为“我的老朋友”的赵超构,江华同样要设法了解其内心思想,真有点草木皆兵,多此一举!何况,赵出言一向谨慎,紧跟形势,即使去交谈一番,也未必会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