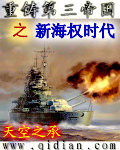重铸清华-第1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怡亲王不认识,但端华穆荫等人都识得是肃顺最为倚重的幕僚,江西人高心夔,端华点点头,“伯足怎么来了?”
“东翁?”高心夔对着端华的话没有即刻回答,只是问着肃顺。
肃顺点点头,“这里的都是自家人,有话直说,无妨。”
“是,今个学生去琉璃厂淘些玩物,恰巧遇到了此次顺天府乡试的几个认识的秀才,他们有些忿然,学生耳朵尖,听到什么‘舞弊’之词,”肃顺身子一震,连忙问道:“可是真的?”
“学生留了心思,特意去龙虎榜下转了一转,”高心夔继续说道,“果然有不少人在龙虎榜下窃窃私语,指着第七名的平龄说此人乃是优伶,且不论有无资格参加乡试,就算参加了乡试,岂能高中第七名?可见其中必然有舞弊之事!”(未完待续。)
PS: 盛夏天热,有几位官长在商议公事,闲聊时谈到天气酷暑,什么地方乘凉最好。一个人说:“有个花园的水阁上很风凉。”一人说:“有个寺庙大殿上很风凉。”有个百姓在一旁叫道:“衙门公堂上最风凉!”众官长惊问:“为什么?”百姓笑道:“那里是有天没日头的处所,怎么不风凉呢?”
三十四、科场弊案(六)
殿内一时寂静无声,众人都被高心夔带来的消息震惊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居然出了这等丑闻?不不不,就算只是一个失误,这也够相关人等好好喝上一壶了!
肃顺目露精光,右手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那道八字胡,“若此事为真,怡王,三哥,”肃顺转向怡亲王和郑亲王,恶狠狠地说道:“柏俊那老小子的死期到了!”
怡亲王对着柏俊观感不算差,沉吟了一会,“老六,这柏俊也是八旗之中难得的才俊,硬生生科举考出来的,如此闹翻,恐怕也是被八旗老少爷们议论,说咱们容不下外人。”
端华看到肃顺铁青的脸色,摇摇头,“怡王,你去天津公干,是不知柏俊新当上了大学士,成日里别人中堂大人中堂大人叫着,还真以为自己是宰相了!对着军机处指手画脚,还对老六冷嘲热讽,最近还上了折子,冠冕堂皇地说军机乃是朝中重地,若非军机下行走之人,还是别去军机处才好,这话不就是对着老六么!”
焦祐瀛差点忍不住,看着肃顺面色不豫,硬生生把笑意吞了下去,憋得脸色通红,载垣听了端华的话,点点头,“的确可笑,若不是老六帮衬着咱们,皇上早就让咱们回家吃自己,再把恭老六请出来了!什么人和老六对着干,那就是和咱们对着干!老六,”载垣对着肃顺说道:“你有什么法子,或者是高先生有什么法子,就说来,咱们听听。”
“伯足,本官欲直接上书弹劾柏俊,如何?”肃顺是直来直往的性子,向来懒得用什么阴谋诡计,反正柏俊如今把柄在外头,自己又是圣眷正隆,何须搞什么小把戏。直接上书弹劾便是。
“东翁,杀鸡何需牛刀?”高心夔在赶来的路上就想好了连环计,“对着柏俊何须东王出发,让几位大人手下的御史上奏便是。如此柏俊也不至于有所防范,到时候皇上必然要请王大臣尚书等人前去调查,那时候,”高心夔笑了起来,“岂不是就是东翁和王爷们说了算的?须知科举之事。向来没有一清二白的,只要去细细翻检,必然有猫腻,到时候,柏俊如何?冢中枯骨而已!”
“好好好,”肃顺听得目光闪动,盯着高心夔连连点头,对着高心夔想出来的法子十分满意,“确实是无上妙计!伯足真乃是本官的卧龙子房也!”站了起来,亲自倒了一杯酒给高心夔。自己举杯相邀,杯中乳白色的汾酒在碧玉杯的映衬下分外迷人,“得高先生,真乃雨亭之幸!请高先生和我共饮此杯!”
“东翁过奖了!请!”
肃顺喝了杯中酒,身子有些摇晃,眼神也混乱了起来“怡王,三哥,各位大人,雨亭醉了,就此别过。伯足,你和各位多喝几杯,大家熟悉下,有什么法子也讲给他们听听?”
“得了。”端华不耐烦地说道,“谁耐烦听这些搞心计的事儿,你们主宾二人商议去便是,到时候该怎么做,叫我们怎么做便是,别耽误我们喝酒取乐子!”
十月份。原本参加科考的士子中间却开始了一场议论引发了风波。原来,士子们在看榜时,发现喜欢唱戏的优伶平龄竟然中了第七名。按清制,娼妓、优伶、皂、吏等不能参加科考,而平龄经常登台唱戏却还能中榜,难免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怀疑。
这场议论持续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消下去的意思。十月十七日,御史孟传金突然呈递奏章,指出此次顺天考试,士子平龄身份不明,录为举人引起物议,同时参劾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一致,应该查究。
杏贞把孟传金的奏折给皇帝时候,原本表情淡然的咸丰皇帝显得很是吃惊,“这柏俊当差得力,乃是两朝老臣,听闻人品也是上佳,方正的很,怎会做这些事?可见是无稽之谈!”
“御史风闻奏事也是职责所在,皇上不必太过苛求,”杏贞不以为然,按照她的看法,这时代的考试实在是漏洞太多了,若是舞弊之事少些,不至于引起士子愤慨,人心不稳,那便不算什么大事了。
皇帝对科举舞弊早就切齿痛恨,决定对这一事件严查。“若是风闻之事,倒也无妨,可到底要给柏俊一个清白,唔,皇后你批:着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人会审查办此案。”
“是。”杏贞又说了几件大事,自己提了参考意见,让皇帝拿主意,皇帝不用看折子,干脆利落地料理完政事,心情愉悦,伸了个懒腰,“有了皇后帮衬着,朕空闲许多,这是皇后的功劳。”
“皇上谬赞了,”杏贞得体地笑道,又说起了宫里的事儿,“听服侍文妃的宫女来报,文妃重阳之后已经卧床不起了,皇上是否要去看她?”
“罢了,她身子不好,叫太医好生保养着,御药房看中什么直接拿过去用便是,朕就不去见她了,你得空去去瞧瞧她,让她安心养病。”皇帝原本就不甚宠爱文妃,这个妃位只不过看在伊尔觉罗氏操劳编撰《咸丰字典》上,给的酬功之举,平时见面也不多话,恩宠,在文妃这里,从来都是没有了。
“是,”皇帝不愿见,那也知道自己去代劳了,“皇上要不要加恩于文妃母家?也让文妃妹妹宽心养病。”
“也好,”皇帝不置可否,不过是一个官位而已,“她父亲彦昌原本是国子监祭酒,就让他去翰林院当满掌院院士吧,他帮着文妃编纂字典,翰林院自然是当得起的,你朱批写给军机去吧。”
“是。”国子监祭酒是从三品,翰林院掌院院士是从二品,乃是超擢了,杏贞十分满意,这下,文妃可以安心养病了,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得宠连累家人而担心。有时候后宫的女子就是这样,除了要博得皇帝的欢心之外,还要为了自己的父亲兄弟的前程而担心,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是宫中宠妃之外普通嫔妃的日常状态了。(未完待续。)
PS: 从前有个地方官,上任伊始,向天神发誓道:“如若我左手要钱,就烂掉左手;右手要钱,就烂掉右手。”不久,有人拿许多银子向他行贿,他很想接受,又怕冲犯了誓言。横思竖想,想出一个办法:叫人拿出一只空盘子,让行贿者将银子摆在里边,然后捧入。那官吏自我宽慰道:“我当时赌咒罚誓是钱,今天收的却是银,我老爷又不曾动手,要烂也只烂掉盘子,与我无关。”
三十四、科场弊案(七)
明清时期,科举考场频频出现的“关节条子”是最时髦的作弊手段,一度有取代夹带、枪替等作弊手段的趋势。
“关节条子”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与考官约定在试卷的某处用一些字眼作记号,并把这些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考官在阅卷时特意留心,凭着条子上的字眼一一对照,完全吻合者就是要录取的考生。当然,考官能如此俯首帖耳地为考生服务,是因为考生在条子上标明了事后给考官的辛苦费。
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手段更是风靡科场。每逢科考,考生们四处奔波,挖门子、找路子,辗转相托,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递上条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时期,不仅考生以递不上条子为憾,考官也以收不到条子为耻。据清代笔记载,考官欣然接受条子,甚至主动索要,或为收拢门生,扩大政治势力,或为了满足虚荣心,似乎收的条子越多,自己的威望就越高,权势就越大。结果,自然是“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科场风气糜烂不堪。
四人的会审团组成后,为保证审讯的顺利进行,咸丰帝还专门传谕主考官柏葰:如果平龄真有舞弊行为,自然要依律惩处,如果无罪,也自有公论。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你只管照旧工作,不必担心,另外为避免议论,你暂且不用入朝觐见。
这一番话软中带硬,绵里藏针,既是安抚又是威慑,可见皇帝查办此案的决心。会审团很快查清,平龄并非优伶,只是平素喜欢曲艺,与那些职业优伶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得中举人,并无不妥之处。但重要的是,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相符合。
墨卷是考生在考场内用墨笔缮写的考卷。科举取士中。为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北宋时就采用了密封、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交上试卷后,工作人员就将考生姓名糊起来,让人用红色笔誊抄一遍。让阅卷官披阅朱卷。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誊抄过程中,要求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誊抄后还有一道程序—对读。其目的就是核对朱卷和墨卷是否完全一致。
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一张卷子就出现了七个错别字,如此低劣的水平,怎么还能被录为举人呢?
会审团抓住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查究,从誊抄人员到对读人员,又到同考官(同考官是协同主考官阅卷的考官,对试卷进行第一次披阅,进行遴选,看到好的考生就向主考官推荐。水平一般的就直接淘汰)。就在会审团开展调查时,此案的当事人平龄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不久竟不明原因地死去,这无疑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平龄的同考官邹石麟供认不讳。邹石麟是翰林院编修,应该说对科场的朱、墨卷制度了如指掌,但在这次披阅平龄的试卷时,以为是誊抄人员手误所致,就顺手把错别字改正过来。邹石麟和平龄素不相识,明知故犯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此前科考中多有类似情况,且都没有被揭发。于是自己认为不会有什么过错,就随手改正了。
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会审团向咸丰帝呈交了处理意见:其一,平龄本人登台演戏系个人喜好,不必治罪。但毕竟登台演戏有辱斯文,谕令士子引以为诫;其二,平龄才华平平,试卷中竟然多处出现错别字,不足以被选为举人,按律应罚停会试三科。因平龄已死,免去此罚;其三,考生舞弊,同考官也应连坐,降一级调任,但邹石麟又擅改朱卷,目无国法,拟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三人也应承担领导责任,罚俸一年。
十月十七日,御史上奏,十八日皇帝下令彻查,二十三日便获得如此结果,结案迅速,而且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原本极为担惊受怕地柏俊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会子终于睡一个安稳觉了,没想到正洗了把脸,敷面的热毛巾还在手上,柏俊家的仆人靳祥进来打千:“老爷,朱尚书到了。”
朱凤标未等柏俊开口想请,就急忙地走了进来,见着柏俊,未行礼就拉上了柏俊的袖子,“中堂大人,中堂大人,”朱凤标此时已经失了自己作为堂堂六部尚书应该有的风姿,声音惶恐,原本平时梳地油光发亮的鞭子散乱开来,“大事不好了!”
“什么大事不好了?圣意不是下了吗?不过是罚俸一年,”柏俊不以为然,心情极好的他现在都开朱凤标的玩笑了,“什么时候桐轩还指望着那几两银子过日子?”
“哎哟,中堂大人!”朱凤标跺脚,“这都是那年的老黄历了!”心急之下也顾不得柏俊的脸面了,“老大人在宫里都是瞎子吗?通政司一个时辰前,收到了肃顺的折子,”说到肃顺,朱凤标有些咬牙切齿,“肃顺说要对顺天府乡试中举的试卷全部进行磨勘!”
靳祥手里的铜盆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残水溅到了柏俊衣裳的下摆,柏俊犹自不觉,丢掉毛巾,一把攥住朱凤标的手,双眼直直地盯着眼前这个前来报丧的户部尚书,“这是真的!??!??”
“中堂大人,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我